经济观察报 关注
2025-09-24 13:33

![]()

如果说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揭示了金融体系的脆弱,那么2020年之后的疫情与量化宽松则让全球经济体暴露出更加深层的隐患:高企的债务、脆弱的财政、不断积累的社会不平衡。全球正在进入一个“债务时代”。美国财政赤字刷新历史纪录,欧元区内部财政平衡日益困难,新兴市场在美元加息周期下外债承压,中国则在房地产调整与地方债问题中寻找新平衡。与此同时,地缘冲突愈发激烈,科技浪潮带来新的生产力跃升,却也放大了国家之间的分化,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冲突。
一个国家的债务及其增长是否存在极限?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是否会破产?倘若会,那又将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的新作《国家为什么会破产》无疑直击要害,深刻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这本书的主题和思路,延续了他在前两本书《债务危机》《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中的一贯关切:经济运行背后的周期逻辑,以及国家兴衰的深层规律。达利欧通过对主要国家的历史长周期回溯和数百年经济数据的统计分析,总结出国家为什么会在看似繁荣的时刻突然陷入财政破产、货币贬值乃至社会动荡的逻辑链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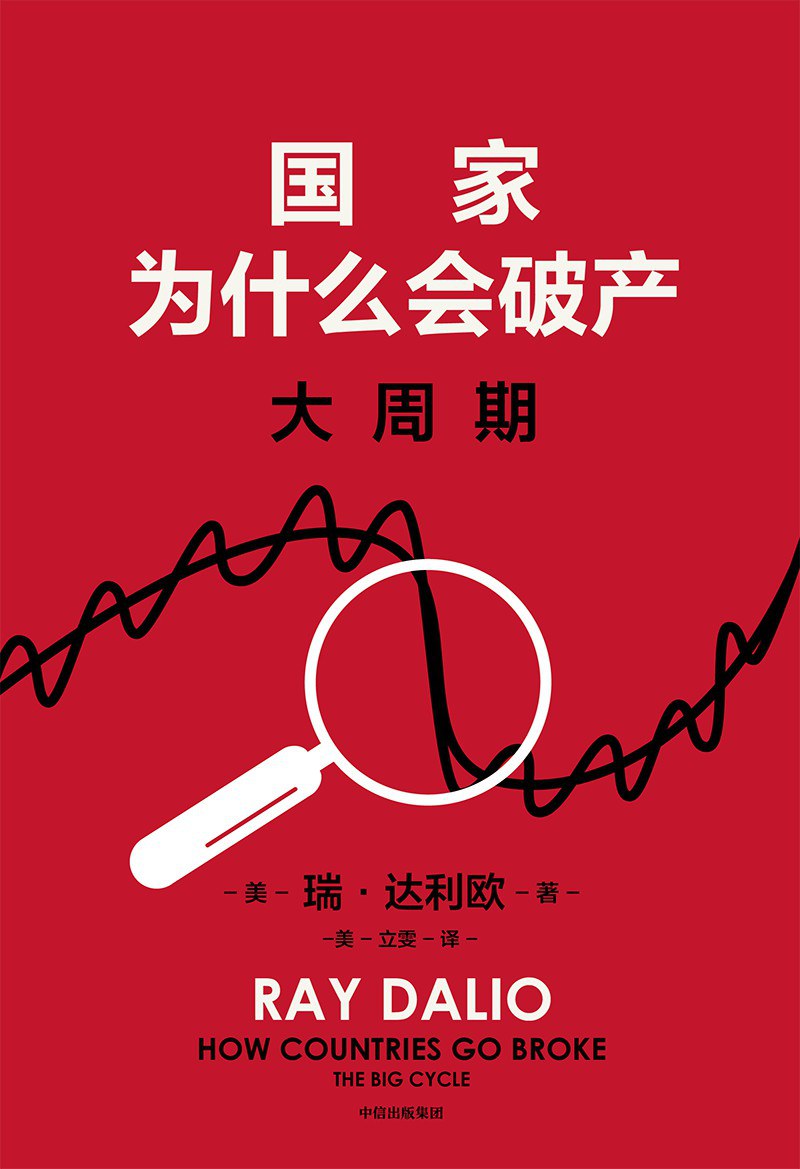
《国家为什么破产》
[美] 瑞·达利欧| 著
[美] 立雯|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6月
这本书值得关注的原因,在于它并非抽象的学术分析,而是带有强烈现实指向的“周期寓言”。
大债务周期:理解国家破产的密码
理解债务周期,就掌握了国家命运的密码。本书的核心概念无疑是达利欧提出的“大债务周期”。这种周期包括短期债务周期和长期债务周期。短期债务周期通常发生于利率下行阶段,此时央行的货币政策会刺激借贷和投资,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指标也随之上升,直到这些指标超出目标水平。而后,货币和信贷供应开始收紧,利率变得相对较高,导致借贷和投资减少,进而造成资产价格下跌、经济活动放缓、通货膨胀回落,形成一个完整周期。这个周期通常持续6年左右,上下浮动3年。正是短期债务周期的不断积累形成了长期债务周期。
短期债务周期和长期债务周期的区别在于中央银行是否能通过政策扭转。具体而言,当债务性资产与负债规模远超收入基数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利率水平必须既满足债权人的收益目标,另一方面又要匹配债务人的承受能力。此时,短期债务周期的经济调节机制因失效而终结,而长期债务周期则因债务负担突破可持续临界点而崩溃。书中强调,国家破产往往不是突然的,而是长期债务累积与制度性幻觉的结果。所谓“幻觉”,指的是社会在繁荣表象下对债务风险的系统性忽视。
达利欧把大债务周期比喻为一种生物或者疾病的演进过程,每个阶段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症状”。通过识别这些“症状”,我们就能大致判断周期所处的阶段,并能够预期未来的发展。一般而言,大债务周期可以被分为5个阶段,不同阶段的货币政策也会随之改变。第一阶段在周期的起点,国家往往处于低负债、高增长的“黄金状态”,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引导信贷流向生产性领域,避免债务空转。当债务增长会推动生产力提升,从而创造足以偿还债务的收入。这将提高人们对财富增值的信心。
第二阶段,债务及投资增长超过了当前收入所能支撑的水平。此时经济增长惯性延续,市场乐观情绪升温,周期滑入“泡沫扩张阶段”,央行的货币政策往往陷入“两难陷阱”——既要维持增长,又不愿刺破泡沫,最终选择“被动宽松”。
第三阶段是泡沫破裂的时期,当经济持续过热,通胀压力突破政策目标,或资产泡沫风险引发担忧时,央行不得不启动加息,但此时债务规模已达高位,利率上升会瞬间放大偿债压力,形成 “加息-偿债能力下降-经济收缩” 的恶性循环。
随之而来的便进入了第四阶段,艰难的去杠杆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社会各部门为了还债不得不选择抛售各种资产,如政府国债、股票等,引起资产价格暴跌,居民减少消费、企业减少投资等。此时央行不得不选择债务重组或者继续增发货币减轻债务压力。当经历了艰难的去杠杆过程后,经济会逐渐恢复平衡并进入第五阶段,新周期也随之开启。此时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从应对危机转向修复增长。
在今天的全球语境下,这一周期模式依旧具有解释力。美国国债总额已超过GDP的120%,赤字仍在恶化;日本在超高负债与负利率之间艰难维系;许多新兴市场在美元周期下外债压力沉重。这里最值得反思的,是达利欧所指出的“制度性幻觉”:在债务驱动的繁荣中,政策制定者、资本市场与公众往往形成合谋,选择性地忽略风险。社会在短期的繁荣中享受“泡沫红利”,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往往是货币信用与国家财政的最终破裂。在长期视角下,这是否正在重演“破产的宿命”?
冲突与秩序:各种周期相互交织
以大债务周期为核心,达利欧在书中又进一步提出“整体周期”框架——他认为,货币政策并非独立变量,而是嵌套在“外部秩序、内部秩序、技术进步、自然灾害”四大文明要素中,这些要素通过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与传导效率”,最终决定债务周期的走向。因为脱离文明要素谈货币政策,就像脱离土壤谈种子生长。因为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国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国家的破产也往往出现在“大国周期”中秩序更迭的临界点,这是外部秩序的表现形式之一。比如冷战时期的苏联就是典型案例:在与美国长期军备竞赛中,苏联将巨额资源投向军事工业,最终导致财政透支与经济停滞,债务压力在体制内部失控,国家崩溃。
达利欧提醒,类似的结构性财政压力,往往是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重要触发点。此外,世界秩序的更迭往往也伴随金融霸权的转换。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十九世纪的英国、二十世纪的美国无不如此。当霸权国在债务透支、货币滥发与金融体系僵化中失去优势时,新的国家往往会崛起。美元的信用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高赤字与政治撕裂让“美元信用危机”的讨论逐渐进入主流。与此同时,数字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等新议题正在重新定义全球货币秩序。达利欧并未断言霸权更迭的必然性,但他指出:金融霸权从来不是永恒的,它背后依赖的是国家财政的可持续与制度的稳定。
内部秩序则围绕着一个国家的政府体制和权力斗争展开。书中谈道:“秩序的变化是由那些拥有最大权力的人推动的,他们决定事情的走向。当那些不掌控现有秩序的人获得了比掌控者更多的权力,并希望改变秩序时,秩序就会发生变化。”当政治极化时,货币政策等可能演化为政治博弈的工具,比如美国两党关于债务上限的问题博弈、美联储何时降息的博弈、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不同时期的治理机制博弈等。在一个国家的内部不同发展时期,金融、政治、军事、法律等力量此消彼长,共同塑造内部秩序。
技术进步作为“整体周期”的一部分,力量不容忽视。纵观历史,科技浪潮确实在多个节点帮助国家走出债务泥潭。十八世纪的英国通过工业革命跃迁,二十世纪的美国借助信息技术维持霸权。达利欧认为,今天的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浪潮,或许能为负债累累的国家带来新的增长红利。然而,他也提醒:科技浪潮并不会自动解决债务危机。相反,它可能带来社会分化与财富再分配的剧烈冲击。如果缺乏有效制度安排,科技红利可能被少数资本占有,反而加剧社会矛盾。
尽管书中对自然灾害的论述篇幅有限,但达利欧仍将其列为整体周期的关键变量——自然灾害通过摧毁经济资产、增加应急支出,倒逼货币政策“被动宽松”,最终形成“灾害-债务-通胀”的连锁反应。书中提到“与其他力量一样,自然灾害也与其他重大力量交织在一起,塑造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例如,发达国家面临的移民问题(气候变化导致的移民压力)和欠发达国家面临的生存环境问题(人们正努力适应干旱、洪水和其他变化)显然因自然灾害的增加而恶化”。
以史为鉴:典型国家的发展经验
书中最引人深思的部分,是达利欧对美国、中国、日本三大经济体的周期性剖析。这不仅是对三国命运的分析,更是对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注脚。
首先是美国,书中回顾了美国自1865年到2025年近200年的发展,揭示了不同周期如何交织。达利欧判断,美国自1945年—2024年共经历了12个完整的短期债务周期,现在正处于第13个周期的约2/3处。这些周期平均长度约为6年,累积形成了一个大债务周期,导致中央政府债务收入比上升,使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恶化。
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债务周期始终与美元霸权深度绑定,形成了“以储备货币地位支撑高负债,以高负债维持霸权地位”的独特模式。美国是当今最典型的“高债务+高消费”经济体。其强大之处在于美元霸权与全球金融体系的掌控力,这让美国能够在赤字恶化的情况下继续融资。达利欧提醒,美国当前的挑战在于财政赤字不可持续,国会的政治僵局使得债务调整困难;美元信用在多极化趋势下面临侵蚀;社会分裂削弱了制度的统一性。然而,美国的优势在于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在AI、清洁能源、生物技术等领域,美国依旧拥有领先优势。这意味着,美国可能通过科技浪潮延缓甚至突破债务周期的宿命。
其次是日本。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努力学习西方的各种制度,而后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自1945年—1990年,日本重建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积累了巨额债务成为资金泡沫,这个泡沫在1989年—1990年破裂,此后一直对日本造成严重的削弱效应。
达利欧认为日本在1990年—2013年采取的去杠杆模式并非最佳,他在书中说道:“尽管日本有能力实施一场‘和谐的去杠杆化’,因为其几乎所有债务都以本币计价,几乎所有棘手的债务人与债权人关系都发生在国内,且日本对世界其他国家还是净债权人,但它的做法与我描述的‘和谐的去杠杆化’应采取的步骤完全相反。”
对于这轮债务周期,日本政府开始并没有积极地进行债务重组和债务货币化,以至于泡沫破裂后对央行和居民的资产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经济长期低迷,通缩压力难解;人口老龄化加速,财政支出刚性上升;政策空间极度受限,对外部冲击缺乏弹性。这一情况直到安倍政府上台后方才有所好转。达利欧认为,日本提供了一个“低增长、低通胀”的生存样本,但这种模式并不可复制。对美国或中国而言,日本更像是一个警示:高债务可能会对应一个长期的“潜在停滞”陷阱。
最后是中国。达利欧认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经历了“债务积累-债务解除-债务积累”的重复过程,导致财富无法积累,也很难产生良好的信贷和资本市场。这一情况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好转,标志是开始构建自主的资本市场。直到今天,社会经济制度已经从一个典型的低效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到一个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他在书中谈道:“我目睹了中国的整个转变过程:中国从努力应对贫困和地缘政治劣势,到通过市场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增长和地缘政治力量,再到如今必须应对这些更大的财富和地缘政治力量带来的挑战,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贫富差距、机会不平等,以及重大的国内和国际冲突。”
达利欧对中国的分析颇具耐心。他认为中国正处于从“债务驱动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面临着地方政府债务压力高企,房地产泡沫尚未完全出清;人口老龄化加速,对财政形成长期拖累;全球地缘竞争环境趋紧,外部增长空间受限等问题。但中国的优势在于制度韧性和社会动员能力。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在危机中往往能集中资源进行结构性调整,这让它在周期反转时具有更强的缓冲力。达利欧判断,债务问题将会是中国发展中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政府有能力实现“和谐的去杠杆”过程,但是能否避免“日本式停滞”,取决于债务处理方式、科技突破与社会治理的平衡。
美国的霸权挑战、中国的转型考验、日本的债务泡沫,都在提醒我们:繁荣与破产之间,并没有永恒的安全区。唯一的出路,在于对周期的认知,以及在科技与制度创新中寻找新的锚。
《国家为什么破产》展现了一种“周期的视角”。它告诉我们:国家破产并非偶然也非宿命,而是取决于如何平衡好债务、内外部秩序、技术进步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对于个人而言,这本书教会我们识别所在国家的债务周期阶段,判断内部秩序、外部环境等要素对货币政策的约束,从而理解债务政策的底层逻辑,规避 “周期误判”的风险,做出明智的决策。正如书中所言:“债务危机既蕴藏重大风险,也孕育巨大机遇。历史证明,它们既能摧毁帝国霸业,也能为深谙其运作规律且掌握应对原则的投资者创造绝佳投资机会。”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