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 Not Fou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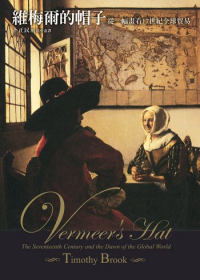
今天我们所称的“荷兰”,原本是尼德兰地区北方七省之一的名字,在1588年,这七个省结成了乌德勒支联盟,现代意义上的荷兰共和国这才发端。摆脱了西班牙的羁绊,在海上贸易方面,荷兰屡占上风,饱受宗教战争困扰的欧洲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17世纪是荷兰的黄金时代,荷兰画家差不多是世界上第一批主要靠中产阶级财力养活的艺术家群体,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收藏绘画在荷兰五大城市——乌德勒支、阿姆斯特丹、台夫特、海牙、哈伦——蔚然成风,执政大员、贵族富户勤于囤画,市井中的贩夫走卒也不惜倾囊购画。
1
按荷兰本土的文化史家约翰·赫伊津哈在《17世纪的荷兰文明》一书中所说:是在一种普遍而强烈的社会需求刺激下,伦勃朗、维梅尔、弗兰克·哈尔斯等人才得以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并向权贵、富人之外的人寻求赞助的。他们的画作也从而洋溢着生活气息,产生了一个被称为“风俗画”的流派。那是一个与英国、法国、意大利那些以宫廷画师执艺术界牛耳的社会截然不同的环境,荷兰画家为了谋生而倍加勤奋,在那短短的一百年里产生的绘画数量,超过了此前所有世纪的总和。
按赫伊津哈的分析,荷兰绘画的鼎盛,以及整个国家在欧洲的异军突起,是因刚刚萌芽的欧洲人文主义新风之故,而传送这股清风的主将也是荷兰人:伊拉斯谟。赫伊津哈还专为他写了本传记,指出,伊拉斯谟的活跃期——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上半叶——可以视为荷兰共和国后来兴旺的前兆,恰如精力充沛、著述不倦的伏尔泰,给他身后爆发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出先声一般。贵为宗教改革的早期领袖,伊拉斯谟谦逊的姿态、怀疑主义的习惯以及对真理和上帝的虔敬态度,和路德与加尔文有很大不同。他的一生与简单粗暴无缘,即使在政治上最春风得意的时期,伊拉斯谟都是用其优雅的仪表和文风来打动人们,而非凭借煽动性的宣讲或国家机器。
如果说内因是人文精神,那么外因就是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荷兰是继西葡两强之后,第三个在地理大发现后尝到甜头的国家,然后才是17世纪中期和“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而位于大陆深处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都要更晚。英国人还不具备出海的能力时,荷兰人就受雇于英王,为他们去海外搜寻资源和宝藏,这些人和邻居欧陆人不同,宁可冒出海的风险,也不肯在陆地上肉搏。没错,尼德兰在十六世纪为摆脱西班牙统治抗争了很久,但即便如此,尚武精神也从来与他们无缘。他们擅长的是商业——另一个场地上、另一种意义上的开疆拓土。
在尼德兰社会,商人是唯一富有经济活力的群体,他们在都市化程度向来极高的七省如鱼得水:没有封建主来阻挠他们自由流动——剥削农民的封建主在尼德兰不存在,贵族们普遍比较质朴,很多也并不富裕,不像在法国和英国那样拥有极大的权力;也没有教会和修道院去钳制社会思想——尼德兰接受基督教较晚,修道院在中世纪欧陆大行其道,在这里发挥的作用却十分有限,从而也没有形成什么强大的政治势力。宗教改革以后,荷兰很快成为加尔文教徒对抗天主教旧势力的桥头堡,被迫害的新教徒和其他异教徒如犹太人等都把荷兰视为宽容自由的港湾,纷纷移居过来。
1 6 世纪是专制主义无所不在的世纪,各国政府都竭力废弃中世纪的自由权利, 用专制体制取而代之。赫伊津哈自豪地说,荷兰是个例外,荷兰人把中世纪最珍贵的政治遗产给继承了下来,它的成功证明了根据古老的地方自治原理建国仍然是可能的。很快,富裕的七省联盟共和国建立了庞大的贸易帝国,经济上继续保持去中心化的传统,商人们得到了充分的经济自由,由此, 荷兰的工商业迅猛发展,在“大国崛起”的名单中占据耀眼的一席之地。那是尼德兰的黄金百年,当周边各国的经济或多或少都受制于战争或国家干预的时候,这个运河密集、海风吹拂的低地小国着实让人嫉妒不已。
2
按美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的说法,17世纪荷兰产生了至少20位名副其实的伟大画家,还有200多位次一等的画家,“但这些所谓的次要艺术家,若放在其他时空,大部分都会跻身杰出艺术家之林。”“伟大画家”的名单里有伦勃朗、维梅尔、塞赫尔斯、弗兰斯·哈尔斯之类,个个名头响亮。然而,这庞大的贸易帝国也好,风靡全联邦的艺术品收藏风气也好,都并没有把每个画家都养成肥得流油的富翁。
赫伊津哈说出了个中缘由:风靡则风靡矣,但艺术之真谛并不为17世纪的荷兰人所懂得,那时诗人的地位比画家更高;执政者给画家们写信,从不掩饰自己的轻傲态度;普通民众也对大多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画家不怀敬意。伦勃朗死时债台高筑,一贫如洗,与他生前身后的荣光都十分不相称;哈尔斯更惨。约翰内斯·维梅尔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管他的36张存世之作今天如何名贵,画家本人终年居于简陋画室,并且年纪轻轻就悄无声息地死在那里,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 维梅尔与那些活着的时候就大获成功的画家——如伦勃朗的弟子杜乌——相比,却是扎扎实实称得上“名垂青史”。维梅尔的每一幅作品,包括晚期方寸大乱后的几张二线油画在内,都得到了大量的复制生产,他的纪念画展在任何地方都能吸引大批观众;在专业领域内,他也是被研究透了的一位画家,卡拉瓦乔的写实手法在他那里达到巅峰,达·芬奇的晕染笔法在他手中有了新发展,他是世界上最早采用点描法的画家。
在卜正民《维梅尔的帽子》一书出版后,维梅尔的伟大还可加上一条:他那妙到纤毫的风俗写实作品里,居然还徘徊着外部投射进来的天光云影。《军官和带笑的女子》中军官的帽子,《持秤的女子》中桌上的银币,《地理学家》中地图和地球仪,《站在一扇打开的窗前看信的女子》中的中国瓷盘和土耳其地毯,此外还有同时代画家范德布赫《玩牌的人》画面中的黑人小男孩——这些维梅尔画中的元素,是一幅渐渐清晰的全球贸易网络上的联结点,这张网渗透进了维梅尔生活了一辈子的、狭小的台夫特世界,甚至钻进了他那栋位于二层楼的简朴画室里。
卜正民管这些联结点叫“门”,一扇扇开往过去,钻进这些门,可以窥看画面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属于北美冒险家萨缪埃尔·德·尚普兰、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巴斯蒂安·科尔库耶拉这类人的,也是属于徐光启、陆若汉这种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的。
这里我们会发现,赫伊津哈所说的17世纪尼德兰社会所体现的“自由”,其实也正在世界其他地方得到边探索边实践。这种实践与暴力的滥用、掠夺与殖民亦步亦趋,它呈现为这一事实: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任何一种联系的建立都必然会经历“不打不相识”的过程。南中__国海是当时因自由贸易而起的纷争的主战场,交火双方往往素不相识,仅因一时眼红于利益而起,帆帷飘飘的商船瞬间成为战舰,商人摇身变为杀人不眨眼的海盗,把别国的船只看成漂浮在浩渺海洋里任人捞取的金锭。
最终,我们可能很难不在荷兰繁荣的分析里补上一条不那么光彩的理由:狡猾的荷兰人成功利用了那个尚未建立秩序的“自由”环境,一旦自己获胜,则立即着手制定游戏规则,那就是日后被视为公法领域奠基性文献的雨果·格劳秀斯的《海域自由》。格氏在文中堂皇地为公海上的贸易自由辩护,究其实质,乃是给他所服役的东印度公司的海盗行径扫清法理障碍。四十年后,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初步确立了欧洲大国的海外秩序时,荷兰事实上已经取代了西、葡两国的霸主地位。
3
然而,真正牵动着所有欧洲人的财富终极欲望的地方却是中国。对于当时的西方人而言,中国还过于遥远、过于神秘,刚刚发现的美洲新大陆,被定性为通往东方的跳板。
中国是一块大磁石,无数小铁屑在中国的吸附下竞相驶出港口,目标是那个有着让西方人垂涎的精美瓷器、白银匮乏、劳动力又廉价的庞大帝国。这个帝国正在内忧外患的压逼下走向崩溃:与日本“倭寇”、荷兰“红毛”以及非洲“黑鬼”的交道,非但没有让晚明政府获得开明的眼界,反而加剧了他们对外界的疑虑和惊惶失措。明清政府从未鼓励国民进行海外探险,受惠于中国人智慧的是他们的敌人。那些来自西欧的亡命之徒前仆后继,掉了一大堆脑袋,推动着海洋文明在与东方农耕文明的较量中战而胜之。
通行于16、17世纪的贸易全球化进程的依然是丛林法则,而“自由”实是大量的木材烧掉后剩下的一小块煤。《维梅尔的帽子》里提到的那些屠杀和盗匪行径的血腥味很淡,因为道德谴责在这里没有立锥之地,对财富的贪欲是驱动世界前行的最核心的动力。哥伦布的残暴,“五月花”清教徒的冷酷无情,乃至耶稣会传教士的狡诈多端,丝毫不亚于科尔特斯之类毁灭拉美原始文明的殖民者,但他们和维梅尔《地理学家》中描绘的那些纯为探寻有用知识的西方科学家一样,属于对人类有“贡献”之人,浑身散发着马可·波罗式的传奇色彩。
对比尼德兰社会,对比海洋文明里那些红着眼的赌徒强盗,不得不说,东西双方同期的表现实在差别太大了。一个三宝太监还不足以让中国地理学家兴奋起来,在绝大多数朝代,他们都“没有改变现状的动力”,因为本国没有那么多远洋商人需要他们不断提供精确的海陆地图,更不用说政__府支持了。而相反,以瓷器鉴赏家文震亨为代表的早期“品位工作者”,他们被授予或自封的使命是完成“化夷”之功——教会西方人如何享用来自中国的奢侈品,从而也激发了后者对东方更强烈的觊觎。
真的很神奇:今天所谓的“地球村”,原来在三百年前就已见端倪——向来固步自封的封建晚期中国人,在西方的诱惑和敦促下,竟也发展出了白银崇拜和烟草需求,从而不由自主地正式进入全球之网,与远在万里之遥的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发生了联系,受到它的驱动、牵制、约束和波及。二百年以后,西方完全强盛起来,大清帝国却被西方人制造的需求彻底拖垮。文震亨一辈子轻蔑西方“化外之民”,视后者为孺子难教,维梅尔《看信的女子》画里那只显眼的瓷盘也许会让他满意;他不曾想到的是,今天自己的国家号称已返归强国之林,但精英人群们却埋头匍匐在了拿刀叉、抽雪茄的“ 野蛮人”礼仪脚下。
- 离想象遥远的童年 2010-11-16
- 老子与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2010-11-15
- 一本忧伤而愤怒的小书 2010-11-12
- 断头台上无温情-评《刽子手世家》 2010-11-11
- 大法官说了不一定算 2010-11-10
 聚友网
聚友网 开心网
开心网 人人网
人人网 新浪微博网
新浪微博网 豆瓣网
豆瓣网 白社会
白社会 若邻网
若邻网 转发本文
转发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