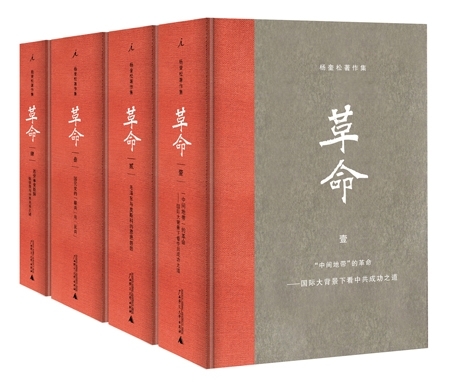
按照其他国家的经验,工人运动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在这方面,共产党的起步较晚,因此也就失去了先机。杨奎松提到,“共产党要做工人运动时,很大一部分工人已经被国民党组织了,还有一部分是无政府主义,他们也有自己的组织。”他以广州为例,广州当时的机器工人,都加入了国民党的工会组织,而更下层的劳苦大众,则是无政府主义,在这种无可组织的情况下,共产党开始组织当地的人力车夫,因此当时的广州,有三大公会,且三个公会之间经常发生流血冲突。“这就可以看出,国民党做工人的基层运动是有一定基础的。”在城市中,共产党一直没能占据主导地位,而“ 国民党在控制城市的很长时间是很牢固的,但是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公会也有他的特点,他比较重视技术工人,比如层级比较低的建筑工人,共产党建国时就发现,很多比较好的技术工人都是国民党工会的骨干。”
国共两党既有其相似之处,在多年的战争与合作中,也一直相互影响。在陈永发眼中,“国共斗争就是两条不同道路的确立。”国民党到了台湾,意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不让最穷苦的农民生活得到改善是不行的。”国民党的土改相对来说是温和的,陈永发谈到,“用温和型的办法做土改能够成功的,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韩日可以成功,是因为长期以来受美国影响,台湾当时的改革是独立的,但一方面与日本留下的基础有关,一方面也得到了一些帮助。”
台湾的土地革命虽然和平,没有流血,但却让地主恨之入骨。与富农不同,地主并不最在乎土地,而是不能接受自己长年来建立的社会地位遭到破坏。提起富农,杨奎松讲起毛泽东年轻时的故事,毛泽东的父亲就是富农,富农都是一点点打拼上来的,靠的是勤俭,“毛泽东帮他爸爸干了一天的活,但家里的雇工可以吃上鸡蛋,做儿子的却没有。农忙时节,雇工吃的比自己家人都好。”而这些在后来的政治宣传中,却不再被提起。
杨奎松总结,“革命这个词,大家用的很泛,其中都有一些改变中国,让中国富强的概念。但他们最在乎的是,你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喊出这个口号。”陈永发也有同感,“国民党垮了那么久,骂国民党很简单”,但真正重要的是,在抗战研究中,“要把国民党、共产党都看做抗战的力量,其中有冲突,但我们必须知道双方都在做什么,想什么,为什么这样想。”
革命被说的太多,被说不完,说不尽,但却不能不提,更不能当做口号来提。
|杨奎松简介|
1953年10月生于北京,1969年随父去湖北襄樊“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入北京第二机床厂当工人,1976年因天安门事件入狱,1977年平反出狱,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2年毕业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编辑,198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讲师,1990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助研、副研、研究员、正副室主任;2001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2003年任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开卷有疑》;《西安事变新探》;《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内战与危机》(《中国近代通史》卷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等专著十余种,并在中国大陆及海外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研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