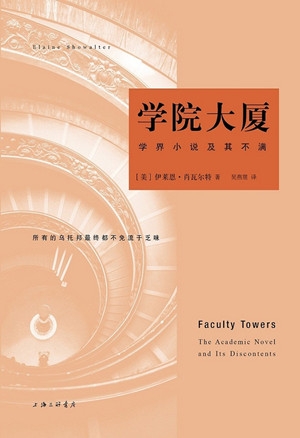导语:通过阅读学界小说……我希望我所学到的,是不要低估学术世界中静悄悄的走道和四方院内的活动,如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奇》中所说的那样,是预计假如我们真的能够对他们的所思所感有那么一丁点儿的理解的话,那我们一定会被那于无声处的惊雷震得目瞪口呆
在过去的50年里,“教授小说”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关于大学的社会历史,以及这个职业在精神、政治和心理上的准则。每一个10年里都有一些关于高等教育的丑闻和新闻标题出现在醒目的地位——阶级、政治上的勾心斗角、女权主义、性骚扰、政治正确。那么,变化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学界小说基本上都属于特洛勒普式的。大学是一个规模不大、颇为封闭的地方,但是跟大社会息息相关,深受它的价值体系和问题的影响,大学甚至成为理想状态的一种模式。20世纪中期的学界小说,胸有成竹地把大学进退维谷的窘境表现为一个个微缩世界:它的政治道德和竞选运动、人文学和科学的划分、个人所承受的在私生活和公共生活以及谦卑的职业和自我宣传之间的张力,这些东西在小说中没有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争吵,而看作是在可以驾驭的范围之内、应对更大的社会问题的方式。如同圣公会的广教会派和高教会派之间就教义和行为而发生的争论一样,教授之间因为方法和理念的不同所发生的内部争吵,看上去都是真心实意的,如果说有些过于激烈的话。总体来说,即便是学术世界中最不受欢迎的居民——《大师们》里的温斯洛和南丁盖尔,《幸运的吉姆》中的韦尔奇(Welch)和马格利特·皮尔教授,《学术园》中的亨利·马尔卡希,《克兰顿的聚会》中的布坎南——也并不阴险恶毒,只不过属于可怜和荒唐而已。而那些最令人钦佩的人物——刘易斯·艾略特(Lewis Elliot)、多姆娜·雷日涅夫、艾德·泰勒、桑迪·桑德令——都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坚定不移,并努力实践着它的学术理想。
但是,到了1970年代,这样一幅学界生活的画面开始变得暗淡,并发生了变化。让人感到反常的是,正当高等教育变得日益壮大,接受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背景和阶层的学生,以满足经济对受过高级培训的工人的要求,以及向上晋升的社会需求的时候,老派教授却犹如维多利亚时代的神职人员一样逐渐被淘汰,在小说中取而代之的是新一代的学者。这一代学者与其说是以信仰和服务为目的,倒不如说是为野心和对权力的渴求所驱动。他们追逐的风尚和发生的争吵看上去越来越微不足道;他们自己也变成越来越丑陋不堪的人物,充满了自我怀疑和自我憎恨。到了小说以性骚扰为主题的时候,这些冲突——关于性和种族问题——已经成为中心的议题,而且意味深长。但是,对于大学应对这些冲突的方式,创作学界小说的作家们则充满了讽刺,认为这些做法古怪迂腐、报复心切、墨守成规以及缺乏人道精神。象牙大厦已经变成了由玻璃幕墙围起来的脆弱堡垒。
在刚开始看学界小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学生,并没有寄希望于跻身大师们的世界,没有指望、更不用说有什么雄心要在这个圈子里出人头地。如今我已经抵达了那个梦想、那个职业的彼岸,进入了学术年历的第五季——退休,从这几十年来阅读学界小说的经历当中,我究竟学到了些什么?它们对于一个教授的现实生活,或者至少对我这个教授所亲身经历的多多少少真实的生活,究竟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总体来说,我认为,当代的学界小说都过于温和,它们用讽刺代替悲剧,用侦探情节取代一个因小社会内部的种种丑闻、内幕、分裂、失望和灾难而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后果。任何一个副教授,只要稍微留点神,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喜剧和悲剧故事,相形之下,就连柯尔曼·希尔克这样的故事看上去也没什么独到之处。我觉得这种把学界心理过于简单化的做法,在近年来以性骚扰占主导地位的长篇故事里表现得非常明显。
让我来举一个在本书中我尚未讨论过的例子,《复仇女神》(Nemesis,1990年),作者是乔伊斯·卡尔·欧茨,她使用的是假名罗莎蒙德·史密斯(Rosamond Smith)(通常在类型小说中才使用)。虽然我算不上是这部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但是,小说有些部分是以普林斯顿大学的英语系里所发生的一桩众所周知的性骚扰案为依据,或是受此案例的启发。小说最初的几个章节描写了在学年伊始,研究生院院长玛吉·布莱克伯恩(Maggie Blackburn)为音乐系的教师和学生举办一个聚会;聚会之后,一位名叫罗尔夫·克里斯滕森(Rolfe Christensen)的名教授对一个叫作布兰登·鲍尔(Brendan Bauer)的年轻男研究生实施了骚扰。欧茨深入地探讨了该丑闻在学术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大学所做出的反应。欧茨是普林斯顿的一位教员,对于学术圈的弱点,多年来她有着犀利的观察,对于大学生活所造成的精神创伤(university trauma),她的分析最为出色、不为感情所动。她能够一如既往地抓住恐惧和闹剧之间的交替变化、恶毒流言的传播网络以及交织在一起的政治上的勃勃雄心和知识上的理想主义。当校园里的流言工厂开动起来对玛吉进行攻击时,欧茨·史密斯对她所感到的震惊有相当出色的描写:“在某些人士中——厌恶女人者而非同性恋者——据传玛吉·布莱克伯恩,一个好斗的女权主义者,开始对罗尔夫·克里斯滕森实施复仇;她跟一个学生串通一气,施展伎俩,使这位年长的作曲家被迫暂停工作。” 玛吉的“朋友们”自然会留意保证她听到这则流言。这个意想不到的情节转折非常有意思,在罗斯和普罗斯创作的小说里,女权主义者和其他一些人设圈套、陷害男性教授的阴谋已经变得必不可少。但是,对于这些流言,或围绕性骚扰案所牵涉到的方方面面的威胁、警告和敌对,玛吉感受如何,欧茨·史密斯并没有继续写下去。旧日的怨恨和偏见而今又重现;在许多系里,人们把相互之间的不了解视为正常的同事关系,如今这层保护盔甲给捅破了,一些人大为震惊,认识到他们对老朋友和老同事是多么不了解,而另一些人则惊恐万分,开始明白同事关系表面上的亲切友好是多么浅薄。在某些人士中,人们做出无情的、清教式的评判,而另一部分人则默默地承受着自责和自我质疑——因为很少有教授不承认教学中存在着两性之间的张力,却能在学术生涯中生存——这两种反应在一个情感色彩浓厚的氛围里弥漫着。
就连欧茨·史密斯也没能全面地捕捉到这种情感余波和错综复杂的感受:荒诞、不公正、愚蠢、悲哀、愤怒,以及伴随性骚扰经历和其他学界丑闻而来的幻灭之感。或许我对这样一本书的要求过高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我们自己卷入一个事件的时候,对于此事的描述,我们读起来会比别人更加苛刻,无论这些描写是发表在《纽约时报》上,还是在一部小说里。《复仇女神》与通常反映学界性骚扰问题的小说之不同,还在于它采用了一个同性性骚扰案——比异性骚扰情节更为令人忧虑、不落俗套。此案的原始素材深深地抓住了涉及男性的核心思想和学界未言明的合同关系,即使是让欧茨以真名来写一部严肃的足本文学小说来涵盖这个问题,那对她也是一种考验。尽管如此,我相信总的说来,性骚扰这个话题所产生的反响,超出了即便是我们当代最优秀的作家所表现的范围。反映这种校园生活的创伤的优秀美国小说,还有待于后人来创作。
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学界小说过于耸人听闻、充满世界末日的悲观看法。跟违纪听证会、或婚外恋、或谋杀情节相比,通常——或者说与此同时——教授们更加关心的是图书馆里有没有我们需要的书。不过,教授的日常生活,大体上不是什么好的故事素材。我还没有看到过一本小说能够真正抓住学术时间的紧张程度,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同时心中怯生生地明白这种工作的永久性,这是一种奇特的结合。任何一个灾难都可能包含着追求名利的意味;要表现那种既工于心计又充满悲哀的情形,对于小说家来说实在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猜想学界小说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具有历史真实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接受学术理想的衰落的同时,也承认体制内产生这种转变的必然性。那些始终生活在体制里的人——那些教师们——对这些变化的感触最深。有这么一种说法,在每个婚姻中其实都有两种结合——妻子的结合和丈夫的结合。(弗洛伊德还会加上姻亲的结合)。在大学里,我认为存在着两类故事——教员的故事和学生的故事。任凭高昂的开支、削减的经费、平权行动的问题、对于标准的种种批评意见,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学术生活依然蓬勃发展。想要并期待着上大学的学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他们在本科学习的经历继续给他们带来满足、欢愉和幸福。今天的本科生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的研究设施、教育机会、咨询辅导、生活安排、奖学金资助、食物和社会选择。在大多数校园里,他们生活得非常幸福;在某些校园里,更是欣喜若狂。
但是,对于教师,我不敢做同样的论断。如戴维·洛奇所说,在大学里教书是一份好工作、美好的工作。但是,它并非完美无瑕。海扎德·亚当姆斯在他杰出的学界小说《赫姆》(Home,2001年)中,运用了一个真正的美国式的乌托邦社会,“赫姆,”暗喻当代的英语系是一个失败的乌托邦。亚当姆斯的身份使其对这些事情极有资格作出判断。他是一位杰出的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同时还是华盛顿大学荣退的比较文学教授。他还创作过另外两部学界小说,以1950年代为背景的《说教的马》(The Horses of Instruction)和以1970到71年为背景的《许多漂亮的玩具》(Many Pretty Toys)。
在《赫姆》中,曾经担任过行政管理工作的历史教授艾德华·威廉斯(Edward Williams)正在研究19世纪的一个叫做“赫姆”的无政府社团,同时还在State主持英语系校外评审委员会(the external review committee)的工作,因此,他不禁看到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他已经开始考虑,若是有一些非常严格的限定,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模式——不是社团的,赫姆式——也许比较合适用来描写”英语系,因为在英语系里,教授们“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英语系与行政管理方面、立法组织发生争执的漫长而多姿多彩的历史,或许如今这世界或者现实只忙于为权力而互相倾轧。” 系里正在为一个美国文学和文化的摩根教授职位(Morgan Professorship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的任命权而奋斗。三年来,它始终坚持不懈地努力着,但一直没能如愿以偿。“其中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意见不和已经变成政治斗争,以至于整个行业似乎都已经被政治化了。种族、阶级、性别、伟大作品的标准、西方文化、多元文化、多样性——所有这些词都围绕着像课程设置或教员的招聘这样最最简单的问题嗡嗡作响。”但是,这种嗡嗡之声掩盖了系里不希望面对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它自身的生存。“真正的威胁来自别处、来自外界:大学日益为以技术为中心的企业所吸收,它会拿人文学科怎么办呢(如果真能的话)。会不会有一天有人来造访英语系,正如他回‘赫姆’一样,却发现它已经没了踪影?”
在21世纪,英语系的衰败和堕落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这不单单是因为商业、科学和技术变得如此之强大,而恰恰是因为英语系已经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目的,而且没有去寻找一个新的知识中心的意愿。“各种各样的中心,”威廉斯想到,“……变得不合时宜已经有许多年了”。他的观点得到了海伦?格兰特(Helen Grant)的支持。海伦?格兰特是研究十七世纪散文的学者,过去曾担任英语系主任,如今一直是State的英语学院院长。戈兰特听着前来参加竞争新职位的各种各样的教授所发的牢骚,不得不“提醒自己,摩根教授这个职位对许多人来说非常重要。她早就知道文学并不是大学所熟知的任何宇宙的中心,如果它曾经是的话”。
然而,系里的成员却表现得他们俨然就是宇宙的中心。就在他们不知不觉地变得越来越落伍的时候,他们继续为这个职位争吵不休,对于牵涉到未来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却置若罔闻,面对来自外界的破坏力量,他们的自我意识远不如乌托邦社会的成员强。由于性骚扰案已经成为表达所有冲突的样板,所以State的英语系也无可避免地有了这样一个案子。弗朗辛·赖特(Francine Wright)是一位信奉女权主义的教授,她怂恿一位本科生向院长投诉,说她在系里的聚会上遭到一位男教授,哈利·威尔士(Harley Wales),对她实施性骚扰。(赖特和威尔士对于任命的问题持完全对立的立场。)事实上,威尔士暗地里是同性恋。在跟系主任格兰特交谈时,那位学生承认她不能肯定确实发生过任何事情而撤销了投诉,随后就休学了。然而,流言在继续传播着。学生们示威游行,要求解雇威尔士;他向赖特提出了诽谤的起诉;两个人实际上动手打了起来。
弗朗辛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是她听任自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她曾经怀着恶意,带着没有根据的仇恨把先前的某些自我置于死地……开始时带着最善意的愿望,信奉正义、公平、凡是正确的一切,可不知怎么,她失去了平衡,陷入了仇恨的境地”。她自杀了。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她的死愈加使她成为校园里的英雄,而完全没能证明威尔士的无辜:“她的声誉越来越高,而哈利?威尔士的则降到了谷底,因为在许多人看来,他似乎依然是折磨她的那个人。这表面上看似喜剧、甚至是闹剧,而系里的一些成员如今把它归为悲剧类型,把弗朗辛作为悲剧的主人公”。
亚当姆斯把英语系成员的斤斤计较、固执己见和不仁不慈,跟赫姆公社成员的勇气、忠诚、热情和团结进行对照,赫姆公社的许多成员因为信仰言论自由而遭到迫害和囚禁。可是,最后赫姆跟英语系一样,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使得个人的独特癖性恶化,进而上升为仇恨”,从而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赫姆》的语气黯然神伤,而不带谴责和戏剧的意味。一群献身于文学、文化、学术和教学的人可以形成一个友谊、慈爱和相互支持的乌托邦社会,这是他们的梦想。然而《赫姆》悲伤地反映了这个梦想的终结。
啊,所有的乌托邦最终都不免流于乏味。当前学界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愤懑可能是夸大其辞,但是,对英语系及其居民或许不抱有田园诗般的幻想,才是更健康、更明智的做法。有爱德华·卡索邦这么一个人做同事,本来也没什么精彩可言,不过,艾略特笔下的学者,如果说冷冰冰、令人生畏,但还是相当有分量和意味深长的。通过阅读学界小说,除了了解关于古根海姆通知信的内幕消息之外,我希望我所学到的,是不要低估学术世界中静悄悄的走道和四方院内的活动,如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奇》中所说的那样,是预计假如我们真的能够对他们的所思所感有那么一丁点儿的理解的话,那我们一定会被那于无声处的惊雷震得目瞪口呆。
by伊莱恩·肖瓦尔特
作者:[美]伊莱恩·肖瓦尔特
译者:吴燕莛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2年08月
在过去的50年里,“教授小说”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关于大学的社会历史,以及这个职业在精神、政治和心理上的准则。每一个10年里都有一些关于高等教育的丑闻和新闻标题出现在醒目的地位——阶级、政治上的勾心斗角、女权主义、性骚扰、政治正确。那么,变化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学界小说基本上都属于特洛勒普式的。大学是一个规模不大、颇为封闭的地方,但是跟大社会息息相关,深受它的价值体系和问题的影响,大学甚至成为理想状态的一种模式。20世纪中期的学界小说,胸有成竹地把大学进退维谷的窘境表现为一个个微缩世界:它的政治道德和竞选运动、人文学和科学的划分、个人所承受的在私生活和公共生活以及谦卑的职业和自我宣传之间的张力,这些东西在小说中没有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争吵,而看作是在可以驾驭的范围之内、应对更大的社会问题的方式。如同圣公会的广教会派和高教会派之间就教义和行为而发生的争论一样,教授之间因为方法和理念的不同所发生的内部争吵,看上去都是真心实意的,如果说有些过于激烈的话。总体来说,即便是学术世界中最不受欢迎的居民——《大师们》里的温斯洛和南丁盖尔,《幸运的吉姆》中的韦尔奇(Welch)和马格利特·皮尔教授,《学术园》中的亨利·马尔卡希,《克兰顿的聚会》中的布坎南——也并不阴险恶毒,只不过属于可怜和荒唐而已。而那些最令人钦佩的人物——刘易斯·艾略特(Lewis Elliot)、多姆娜·雷日涅夫、艾德·泰勒、桑迪·桑德令——都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坚定不移,并努力实践着它的学术理想。
但是,到了1970年代,这样一幅学界生活的画面开始变得暗淡,并发生了变化。让人感到反常的是,正当高等教育变得日益壮大,接受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背景和阶层的学生,以满足经济对受过高级培训的工人的要求,以及向上晋升的社会需求的时候,老派教授却犹如维多利亚时代的神职人员一样逐渐被淘汰,在小说中取而代之的是新一代的学者。这一代学者与其说是以信仰和服务为目的,倒不如说是为野心和对权力的渴求所驱动。他们追逐的风尚和发生的争吵看上去越来越微不足道;他们自己也变成越来越丑陋不堪的人物,充满了自我怀疑和自我憎恨。到了小说以性骚扰为主题的时候,这些冲突——关于性和种族问题——已经成为中心的议题,而且意味深长。但是,对于大学应对这些冲突的方式,创作学界小说的作家们则充满了讽刺,认为这些做法古怪迂腐、报复心切、墨守成规以及缺乏人道精神。象牙大厦已经变成了由玻璃幕墙围起来的脆弱堡垒。
在刚开始看学界小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学生,并没有寄希望于跻身大师们的世界,没有指望、更不用说有什么雄心要在这个圈子里出人头地。如今我已经抵达了那个梦想、那个职业的彼岸,进入了学术年历的第五季——退休,从这几十年来阅读学界小说的经历当中,我究竟学到了些什么?它们对于一个教授的现实生活,或者至少对我这个教授所亲身经历的多多少少真实的生活,究竟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总体来说,我认为,当代的学界小说都过于温和,它们用讽刺代替悲剧,用侦探情节取代一个因小社会内部的种种丑闻、内幕、分裂、失望和灾难而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后果。任何一个副教授,只要稍微留点神,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喜剧和悲剧故事,相形之下,就连柯尔曼·希尔克这样的故事看上去也没什么独到之处。我觉得这种把学界心理过于简单化的做法,在近年来以性骚扰占主导地位的长篇故事里表现得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