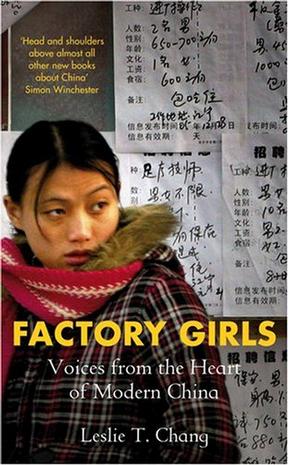
Leslie T. Chang(张彤禾)/著
Picador USA
2009.02
by张彤禾
1.
十九世纪下半叶,华北遭遇干旱和饥荒,逃荒的人使得东北的人口开始膨胀。我的家庭也在这次经济急速发展中脱颖而出。我的曾祖父张雅南,买了一个榨油厂和一个面粉厂,运用这投资赚来的钱成为六台最大的地主。1890年左右,张雅南监督建造了一座有五个堂屋八个厢房的大宅院。祖先的牌位和画像占领了堂屋,而活人则在厢房里吃饭、劳作、睡觉。中国家庭就是这样生活的——死人把活人挤到一边,而恪守孝道则嵌入到每一个房子的建造工程之中。这个宅院被命名为“新发源”,意思是“新的发源地”。宅院四周有高墙,毛瑟枪从每个角落的高处伸出,还有武装民兵保护它不受强盗侵犯。一个家族有多富裕要看这个家吃的是什么,而在新发源,即使是雇来的帮手也能吃上豆沙包。
1898年我的祖父张春恩出生,几乎村子里的每个人都姓张。从幼年起,他在家里的私塾上学,长篇大论地背诵上溯到孔子时期的四书五经。这些文字他懂不懂并不重要:教育是要塑造一个孩子循规蹈矩的言行举止,早早地灌输他温良恭俭的美德。学习的终极目的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朝廷命官——这个制度基本上持续不变已长达一千年。
但那个世界在我祖父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已经开始土崩瓦解。十九世纪和西方的接触让中国碰得遍体鳞伤;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在两次鸦片战争失利之后,清朝君主被迫签订了一连串“不平等条约”,开埠通商,给予西方列强和日本经济和法律的特权。国内改革派人士大肆谴责传统教育造成了中国的屈辱衰落。他们的努力终于在1905年正式废除了科举制度,各地开始设立传授现代知识的新学堂。1911年,我祖父刚刚十二岁,清朝覆亡,共和政体取而代之。
我的祖父还是个孩子时,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家了——和现在一样,所有通往成功的道路都是指向村外的。他的哥哥张奉恩以后有一天会主持家业。但是作为正房的第二个儿子,我的祖父占了个优势:他可以离开。1913年春天,他入读吉林中学。这是本省第一个教授新学的学校,它略过传统的四书五经而主张教授数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三年之后,祖父离家去上北京大学,全国现代学校系统的翘楚。
当时北京大学的多数学生来自沿海一带富裕的商贾家庭;我的祖父是个局外人,有些像个科罗拉多州采矿小镇拿奖学金的孩子出现在哈佛大学。和我祖父同时期在北大,有位在图书馆工作的,名叫毛泽东。
如果传统的价值体系完好无损,我祖父很可能取得大学最高学位,顺利地在政府找到工作。但是新学已经把他带往意想不到的方向:祖父获得一个省级奖学金,送他去美国留学,于是他念完大二就退学了。他娶了一位叫李秀兰的年轻女士,是家里给定的亲——婚后第三天,他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
我的祖母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学院读书,这也是全国最早收女学生的院校之一。她的本科是体育和音乐。她参加学生示威游行,抽烟,还改了个新名字:李芗蘅, 她喜欢这两个更罕见的字。毕业之后她在省会吉林市一所高中教书。
2.
我的祖父1920年到达美国。那是个私酿金酒,爱抚晚会和黑帮教父的时代,但是他简直没注意过这些时髦事。日记的字里行间都是关于他探索值得学习的课程和中国的政治局势。这两个主题相互关联:通过在美国掌握正确的技能,他才了解能帮助祖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必备的知识。他心不在焉地学了点儿文学和经济学,最终锁定了采矿工程:发展工业必能拯救中国。
几千个中国学生在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去到美国,这也是最早的出国留学大潮。他们视西学为帮助中国最有效的办法,因此倾向于学习实用的学科,比如经济学,自然科学,尤其是工程学科——从1905~1924年间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国留学生选择了工程学。我的祖父在密歇根矿业学院求学,那里靠近加拿大边境的一个古老的铜矿地区。他于1925年毕业,全班四十四个学生中排名三十三。显然对他,新学很不容易应付。
我也是偶然发现祖父的日记。我父亲说家里这些年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内战、去台湾、来美国,他们把一切家当都弃之不顾了。我开始调查家史一年多以后,我和父亲通电话,问他有没有属于他父亲的东西。意料之外的是,他说他身边有两本日记,一本是我祖父在美国写的,另一本是全家战时住在重庆时写的。两本日记大概有一千多页。“没什么意思,”我父亲说。“他就写了一些像是‘今天日本军队逐渐逼近城市’这样的东西。”“其实,”我说,“那很有意思。”
透过他日记的字里行间,我逐渐了解我从来没见过的祖父。他是一个上下求索的年轻人,梦想能从事各行各业。他像农民工一样干一行,换一行,很快心生厌倦又很焦虑他学得不够。他孤独寂寞漂泊无定。自强是日记里不变的主题。完成学业后,我的祖父在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工厂和矿山做了两年实习训练。他在芝加哥上夜校学习电机。一篇篇日记里零星夹杂着他想要记下的陌生单词:古德曼标准短壁机、水泥沙子炉渣比、金字塔泵平炉搅拌机高炉波纹底架门。
在美国的那些日子,我的祖父改了他的中文名字。新选择的汉字,莘夫,出自一个古老的成语,莘莘征夫,翻译过来就是“许多勤勉出征的男子”——我的祖父立志成为这样的人:一大群人,致力于尽忠服务,而自我则消隐在名字里。
祖父在1927年夏天回到中国。他回家的第一天,他的父亲在村里办了一场接风庆典,庆祝他最宠爱的儿子千里迢迢从美国给家里带回荣耀。第二天,一家之主拿出一根叫做“家法”的木棍——传统的家庭用家法来惩戒小孩和佣人——打了他一顿。在美国,他的儿子从文学专业转到学矿业工程,而竟不先征得家长的认可。姑且不论这位父亲远在一万公里以外,加上对美国大学体制毫无所知。在中国家庭里,父亲的话就是法律。这一顿好打,我祖父好几天都不能坐下来。
他的父亲想要他留在家里帮忙管理家业,但是这个年轻人拒而不从: 他厌恨张家大院生活的纠葛,很高兴能逃脱。他在中国遥远的东北哈尔滨的穆棱煤矿得到矿长的职位。
1931年,日本军队长驱直入东北的南端。六个月内,日本军队占领了整个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日本人来了之后,我的祖父到了关内。
1937年战争爆发的时候,我的祖父在河南一个煤矿当矿长, 他帮忙把设备从河南运到八百公里外的四川内陆。作为国家资源委员会——负责战时建设国家工业基础的政府机关——的一名官员,他被派遣到偏远矿区,监督战略性物资的生产。他通常会先去到一个地方,等到情况安定时再给我祖母写信。五个孩子,一个个都出生在边远的矿业城镇。老大蔼蕾出生在哈尔滨煤矿,那时我的祖父从美国回来后在那里工作;我的伯伯立豫和我父亲在河南中部的煤矿地区出世。四川煤矿,小姑姑蔼蓥出生;湖南汞矿,叔叔立程。我祖父的理想主义在这些与世隔绝的地方留下足迹。大多数留学归来的学生生活在大城市,但是祖父认为他的工作在国家相对落后的地方更有意义。
个人关系被切断了——在战争的混乱局势中,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一家人会到一个新的地方,刚送孩子入学,接着几个星期之后又离开。伯伯立豫跟我说,他小学六年搬了七个地方。和农村老家联系非常困难:写给东北的家书必须绕远路避过封锁线。更令人惊奇的是,人们这样还能再次找到彼此。战争快结束的一天,一个叫赵鸿志的很帅的大学生走进重庆矿业局员工餐厅,认出了我的祖父。他家和我们十多年前在河南煤矿就有了交情。赵鸿志受邀到家里吃晚饭,并开始追求我的大姑姑, 他们从小就认识。
战争期间也有家人重聚。我祖父的哥哥留在家里照顾家业,他的儿子张立教, 到北京上学,当时我的家人也住在北京。传统中国家庭里,亲兄弟和嫡堂亲是一样的亲。我的祖父祖母给立教住的地方,给他付学费;我伯伯和我父亲从孩提时候就学着向“立教哥”看齐。以后为躲避日军进犯一家人搬到重庆的时候,立教也和他们同行。
对我的祖父来说,战争时期令人沮丧。战争不光夺取生命造成毁坏,工作难以为继,事业中断,交通阻隔。偶尔他也会怀疑这样工作是否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