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图虫网)
高鑫源/文
“劳动光荣”,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不过近来,对工作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加班文化、内卷文化渐渐流行起来,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躺平”的文化。实际上,劳动者对工作的质疑,更为准确的是对畸形工作现象的质疑。
徐志伟与王行坤主编的《“后工作”理论》一书所收录的16篇文章时间跨度超过百年,梳理了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对劳动与工作问题的各种追问,总体来说,这些文章不断追问的问题有三个,当前的工作怎么了,为何令人生厌;何为有意义的工作;如何实现有意义的工作?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对工作合理化的探求。
一
为了回答上述三个问题,编者将16篇文章分为四辑,从最开始对闲散问题的追问着手,通过对人类学的挖掘,确定闲散的合理性,并结合当代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拒绝思想,最终将落脚点定在对后工作社会的展望上。
对工作的批判,首先是建立在工作的异化的基础上的,为此在本书的第一辑中,编者收录的四篇文章主要从反工作伦理的角度切入。老板要求职员下班前上传手机实时电量截图、员工朋友圈抱怨工资即被老板辞退……劳动原本在马克思的思想是促进人自我发展的手段,在当下却成为了福柯笔下的规训手段,劳动者们被迫发明出种种“摸鱼”的哲学,消极怠工看似是在反抗,实际上只是一种生产的延迟,并没有对异化的工作采取绝对的拒绝态度。
在此辑中,对拉法格“懒惰权”的强调,其实涉及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一个重大区别,当前的工作到底是对劳动力的重视,还是对劳动的重视。资本的运作可以称之为是一个计算过程,无论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都能看出资本对处在生产过程中的人的计算,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活动并非是单纯的劳动,而是将人转化为劳动力后融入对成本、利润以及耗损的精细计算中,劳动对人的发展并不能在此过程中体现出来。相反,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对更少的工作和更好的工作的需求,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劳动就是一个不断减少的因素,“懒惰权”以及威廉·莫里斯所谓的工作与劳碌的区分,都体现了对工作异化的批判,只有放下手中的异化工作,才能够追求自我的完善。
对工作的拒绝使人们拥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中外都流行对闲暇的反对,中国的“不劳动者不得食”与西方伊甸园中亚当夏娃被惩罚必须汗流浃背才可获得食物,两者在肯定劳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闲暇似乎是一种罪过,但在《“后工作”理论》中,编者选了卡尔·波兰尼与马歇尔·萨林斯等人的文章。他们强调说,在原始部族社会中,虽然物质的丰富程度远不如现代,但是他们不像现代的人一样,一天加班工作超过12小时。甚至于像乔纳森·克拉里所言,当前的劳动者已经失去了睡眠,成为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连轴转的生产机器。原始社会的人们,采集狩猎的时间仅占一天的三分之一不到,比现代人一直呼吁而难以得到的“八小时工作制”更短,却足够供养自身,并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而现代人日夜工作的情况下,却连自己的生计都难以解决。
这些学者的观点是有趣而又惊人的,这表明闲暇并不是一种罪过,罪过的是工作本身,当现代社会机器为了维持运转而不断吸收劳动力时,也在不断创造工作岗位,但是新的工作岗位所配属的,却都是一些“狗屁工作”,工作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在狗屁工作中,规训的就如同魅影一般持续不散,当人们被狗屁工作缠绕之时,便失去了闲暇。失去快乐与创造力的行尸走肉,对资本与权力而言是最温顺的宠物,大卫·格雷伯的“狗屁工作”也从反面说明:是彻底的闲暇而非小打小闹的“摸鱼”式延迟,才是对异化劳动的真正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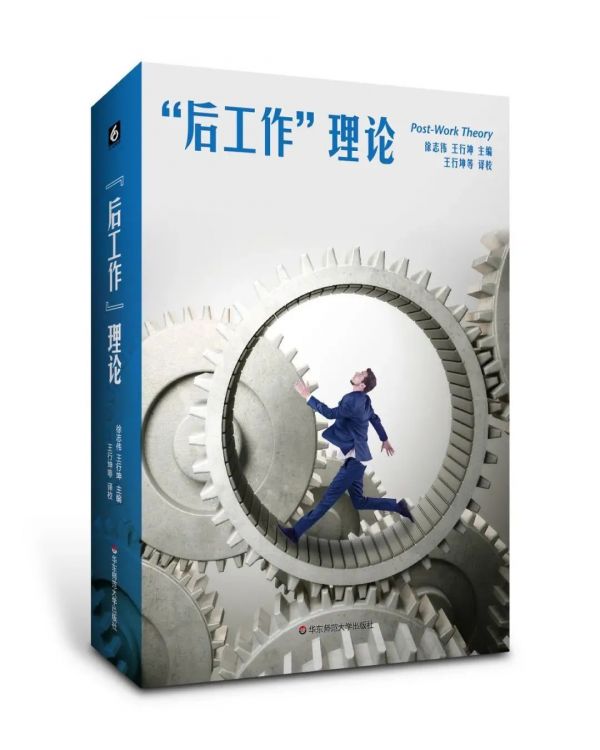 《“后工作”理论》
《“后工作”理论》
徐志伟 王行坤 /主编
王行坤等 /译
六点图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1月
二
相比前人对异化工作的种种批判,1960年代是一个风云的年代,在此后的十数年间激进左翼对工作的批判,采取的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彻底而决绝的态度。期间,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德波等人高喊“绝不工作”,而在意大利,奈格里等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也在思考拒绝工作的相关思想,对工作的拒绝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过去,人们拒绝的只是工作的异化部分,但是在自治论者们看来,唯有对工作的全盘拒绝才能够摆脱工作的意识形态影响。自治论者将对工作的分析重点并没有放在工作或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而是放在价值如何引导劳动实践的调整过程中,由此观之,西方盛行的工会游行便成了一种笑话,成为了让躁动的工人重新回到岗位上的一支镇定剂,一切改善工作环境与待遇的措施都是资本玩弄的把戏,拒绝工作就是要拒绝这个社会将工作视为社会运行的中心环节,人们不再将工作视为个人生活的中心,追求生活多样化的大门便会敞开。换句话说,自治主义者的拒绝工作并不是像过去的社会行动者与理论家那样要求解放工作,而是从工作中解放出来。需要明确的是,自治论者的想法在当时语境下是没有实现可能的。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拒绝工作后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但从工作中解放出来投身政治也是陷入另一个牢笼之中,真正的解决之道仍然是在社会根本体制的变革上。
本书的最终落脚点放在探求“后工作”的可能上,虽然自治论者的看法多少有些不切实际,但是“后工作”时代确实是慢慢向人们靠近了。当然,也许有人会反驳,更充分的就业与更灵活的工作时间这些在当前已经实现了,“零工经济”就是如此,滴滴司机、外卖配送员以及大部分的钟点工都是如此,人力成本的提升,这些人通常也能获得更高的收入。
确实,不可否认的是这类“零工经济”确实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经济类型,但是,互联网并不是一个新奇的事物,平台资本主义对他们的压榨依然存在,配送时效、抢单速度等可量化的指标仍然压榨着劳动者,社会上对这些职业仍然不能平常看待,常常出现硕士或博士外卖配送员被人们惊呼浪费人才,这表明职业平等观念未能得到贯彻,体面而有保障的工作并没有完全实现。
“后工作”理论认为工作最终将走向灭亡,但这已经和奈格里在意大利的呼吁有了根本的不同,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制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会随着社会发展而走向消亡,但是工作不会。马克思反对雇佣劳动,但不反对工作本身,失去了雇佣性质的工作,将成为人们完善自我发展自身的方式,而非换取生计的手段,因此,“后工作”社会的工作如能向着马克思的方向前进,也许就不再是天方夜谭。
至此,《“后工作”理论》对开头提到的三个问题进行了回答,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被工作包围的时代,而异化的工作正剥夺着劳动者应有的关于创造的快乐,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成就自我的作用的。为此首先要强调不工作的正义,对现行的工作体制说“不”,进一步地,在当前要将这种不工作的正义融入到追求工作的合理化的进程中,只有更有保障的工作,才能实现工作对人的正向促进作用,最终达到马克思所谓的“消灭工作”的程度,《“后工作”理论》的选文表明,更好的工作与更少的工作两者并不冲突,“后工作”的未来是人们可以设想的一种合理的未来。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