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关注
2025-09-19 18:5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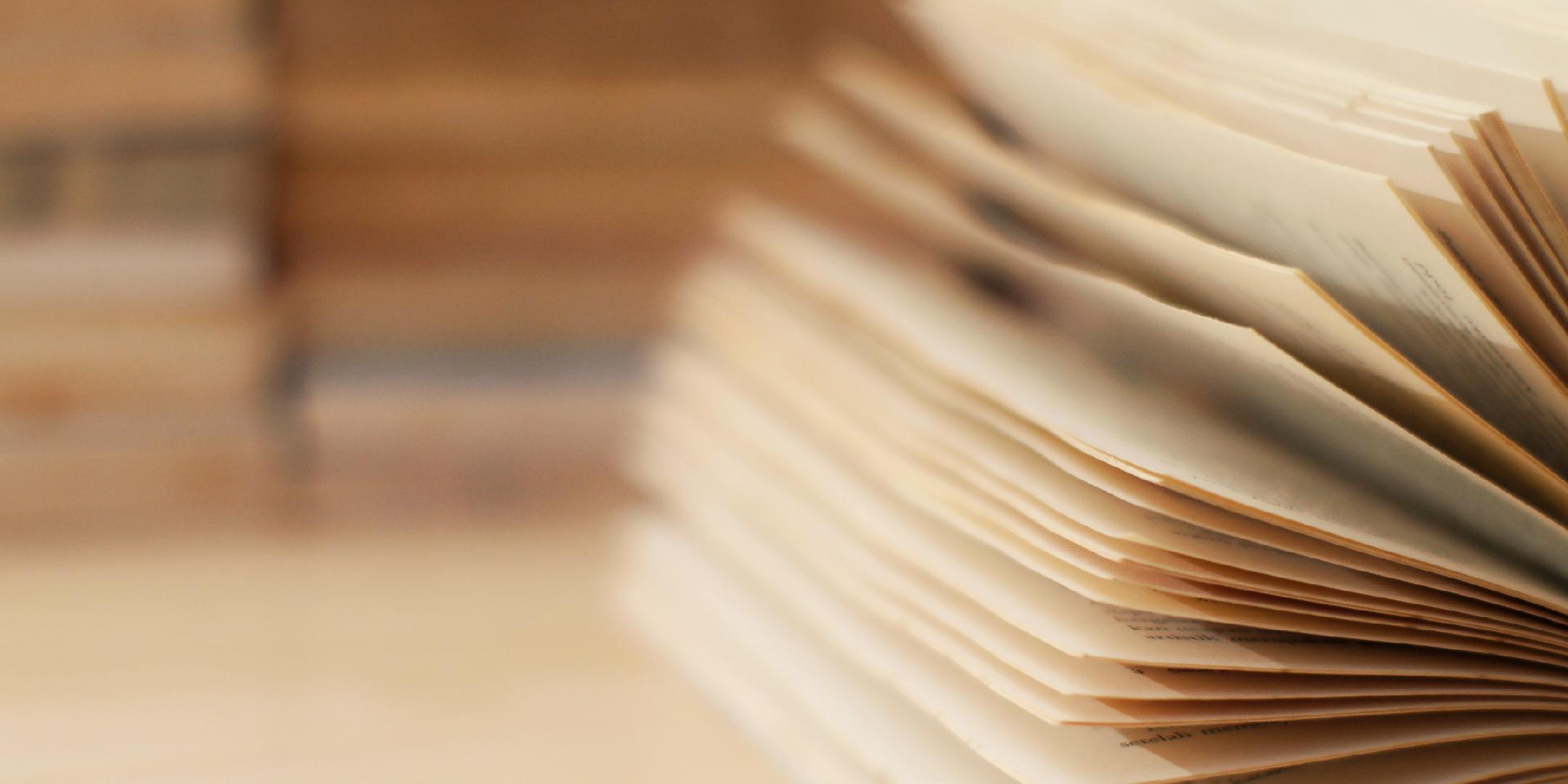
文/张修智
1935年,蒋廷黻应蒋介石之邀,辞别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之职,躬身入局,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这是一个副部长级别的职位,且位居中枢,故显赫而重要。赴任前,胡适以“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不比在山清”两句诗赠送蒋廷黻,意思显豁,劝其不要去蹚政治这道浑水。胡适的意见,也代表了许多蒋的朋友的看法。
不过,朋友们的好意显然没起什么作用。在《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出版)中,写到从书斋一跃而进政治中枢,蒋廷黻没有表现出一点犹疑,仿佛是一件期待已久的事,并且在政坛一干就是近30年。这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一职前的排距、彷徨且兑现了卸任后即返回书斋生活的诺言相比,形成鲜明反差。
对于出山之水的清浊,蒋氏晚年在回忆录中并没有做自我评判,他只是列举了几件自己主导、推动的改革事项,用事实说明自己做过的努力,同时慨叹行政改革之难。看蒋廷黻上任之初的举动,不能不令人感叹这位书生政治家的憨直与天真。他的头几板斧,就砍向了中政会与机构改革。中政会是何方神圣?它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简称。根据规制,国民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行政院于周二院会上所做的重要决定,都要送到中政会周三的会议上讨论。显然,中政会是党国体制的灵魂。但在蒋廷黻看来,这个议事程序是可笑且低效的。中政会的人员对问题的了解程度远不如行政院的人员,但行政院起草提案的人员却大部分不能出席中政会,因此对提案既没有说明也没有辩护的机会。他认为,行政院与中政会的关系应予调整,中政会讨论提案时,各部会的首长要亲自出席。蒋氏的用意,显然是想增加第一线工作人员在最高决策程序中的权重。其实,对于中政会与行政院这种繁琐、低效而不专业的关系,其他人未必看不出来,他们只是不说而已,只有蒋廷黻这只初生牛犊,才会不识时务地要去太岁头上动土。
机构改革从来是块硬骨头,蒋廷黻对此也不惮展开风车大战。他首先提出取消经济委员会和建设委员会的动议,认为这两个机构本身职能重复不说,还与其它机构也有重复。他还提出设立农林部、合并铁道部与交通部等方案,认为农业立国的中国不该没有一个专门的农业部门。
蒋廷黻推动的这些改革,都属于敏感而高难度的动作,多没有立刻见效。但一年后,蒋廷黻在驻苏联大使的任上发现,经济委员会和建设委员会真的被裁撤了,铁道部与交通部被合并,而农林部也成立了。
不过,蒋廷黻的生猛作风,显然还是把蒋介石吓到了。蒋廷黻在政务处处长这个位置上才干了几个月,刚刚提交了中央政府的改革建议稿,蒋介石即把他的位置与翁文灏做了对调,让后者负责中央政府的改革工作,而让蒋廷黻负责地方行政改革。半年多后,蒋廷黻又被派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一职。中国近代外交史是蒋廷黻最擅长的史学研究领域,他也可以说是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人,让他出任驻苏大使一职,虽有将这头“闯入瓷器店中的猛牛”(翁文灏评价蒋廷黻之语)引开之意,但蒋廷黻确是这一职位的一时之选。当时国内普遍寄希望蒋廷黻能设法让苏联与中国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侵略。然而这是不切实际的期望。苏联奉行西线优先的战略,它对中国的支持,限于中国能在远东拖住日本,使之无暇无力进攻苏联为止。蒋廷黻在驻苏大使任上难有耀眼业绩,不到两年,又重回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的位置上。
重作冯妇的蒋廷黻,并没有改变自己不怕得罪人的行事风格。比如在编制各省1942年的年度预算时,他坚持对预算做合理化的改革,结果他主持编制的各省预算案几乎招致了所有封疆大吏的反对。不过蒋廷黻并没有让步,幸好他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让预算案得以通过。《蒋廷黻回忆录》只写到一半,蒋氏便去世了。尽管他没来得及在书中对自己不短的从政生涯做总结性的评价,但不难猜想,他的自我评价不会多高。毕竟,他登上的,是一艘十几年后即沉掉的船,而这期间,他始终是驾驶舱中的一员。在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土崩瓦解的大背景下,任何曾经的改革尝试与努力都不免黯然失色。《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在评价南京十年(1927-1937年)国民党的统治时认为,从南京政府的建立,到全国卷入一场漫长和毁灭性的战争,国民党统治只经历了十年时间。十年的时间对于建立一个全新的全国政府,扭转长达一个世纪以来冲击着中国的政治分裂和民族耻辱的浪潮,是嫌太短了。因此,尽管该书肯定了南京十年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以及国民日渐增长的自信心,同时也特别肯定了蒋介石政府中不乏受过教育、具有现代思想的文职领导人这一事实,但依然认为,这一切无补于大局。“自1935年以后,蒋介石使一批受人尊敬的银行家、记者以及知识分子进入其政府:其中有张嘉璈、翁文灏、吴鼎昌以及蒋廷黻,他们才能出众而且比较进步。然而,这些新来的人,只对政府的基本政策产生了轻微的影响。在事实上控制着政权的人中,懂得如何去完成社会和经济重建的任务的,只是凤毛麟角。”《剑桥中华民国史》揭示的这一事实,与蒋廷黻的观察不谋而合。回忆录中,他以切身体会说:“侧身政府的人中存心克尽厥职的,固然远较一般人想像的为多,但政府官员中具有现代眼光的却远较大家想像的为少。”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蒋介石之所以招揽蒋廷黻这类知识分子入阁,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而已。这是一种简单化、污名化的理解。事实上,蒋介石之所以这么做,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内心的危机感。1936年10月,蒋介石曾断言:“如果我不清除现在这个腐败黑暗、行贿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愚昧的机体,并代之以建立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那么,反对我们的革命不久就会爆发,就像我们发动反满革命那样。”(《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181页)这种深重的危机感,才是理解他延揽包括蒋廷黻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进入政府的真实动机,也是理解蒋廷黻称自己为蒋介石的“政治看家犬”的一把钥匙。蒋廷黻最要好的朋友,如胡适、傅斯年、翁文灏、浦薛凤等,对蒋廷黻的个性或许有批评,但没有人认为他是因为一己之私而从政。只是,蒋介石终非一个具有现代眼光的政治家,他的局限,决定了蒋廷黻们的作为也只能是非常有限的。据看过蒋廷黻日记的美籍华人学者江振勇先生披露,蒋廷黻在日记中多有对蒋介石的不满、批评之辞。
读《蒋廷黻回忆录》,最受感染的地方,是蒋廷黻心中那种真挚、浓烈的家国情怀,那种渴望自己的国家走上现代之路的深刻情感。这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共有的精神特征。古语云:“恩怨尽时方论定”。蒋廷黻们置身的那种天地玄黄之争,距今已近一个世纪了,今时之人,完全应该在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现代化转型这一宏伟坐标下,去观照、评价蒋廷黻们的努力,从而报之以温情与敬意,如是,就会避免那种穷形恶相的史学。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