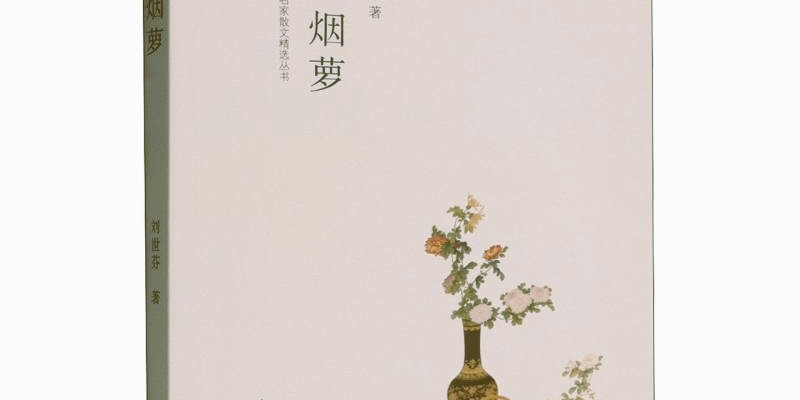
一个画面,根植脑海许久:读过旧私塾的父亲,戴一副老花镜,捧一本黄旧的“老书”,读得津津有味。那本旧书,竖排,繁体,封面残破,但被父亲用一张不知从何处寻来的粗纸包裹,经常脱落,缺了一角,粘了泥土,甚至落上一粒变形的高粱米……后来,将要散架的时,父亲索性找来一块破布,保护着那本“行将就木”的书。
对于尚未识字的我,父亲手里捧读的,等于天书。有时转到父亲身后,看他用钢笔在字间划着,手指间尚存刚从田间带回的土屑……他手中的书并不固定,当我认字之后,可以辨出有时是《资治通鉴》,有时是《隋书》,肯定还有别的,只是我的记忆已被时光掐断。唯一难忘的是他那个捧读的姿势。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匮乏,全家人三餐无继,父亲的阅读似在告诉我:书页上的文字比吃食金贵。
当我渐渐长大,能认出书页上的些许文字,这样的画面就有了重量。
一本破旧的繁体四角号码字典,或者说,我是“读”着这本字典,叩响了文学之门。
彼时的乡下,原始、贫瘠、动荡,果腹成为所有人的第一要务。父亲给这个家庭营造出一种奇特的文化氛围: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的同步奇缺,使得这个家庭笼罩着一种有别于邻人的别样的重度饥饿。一方面,父亲每天眉头紧锁为全家的肚腹奔走,及至夜灯如豆,他又一字一句地教我背诵四角号码口诀:横一竖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对于求知若渴的农村孩子,平时见过的文字本来不多,只好先囫囵吞枣地熟记口诀,然后对照字典扉页里的图形,一笔一画地揣摩、对比,很快,我居然能够熟练地使用了。
由于这本字典,我过早地完成了繁体字启蒙,高中暑假的时候,父亲为我借来一本繁体《红楼梦》,内容虽似懂非懂,但阅读却毫无障碍。有一点可以肯定,从这本书开始,正式开启了我的读书生涯。
我的阅读之路,嗷嗷待哺,一直“营养不良”,这种缺憾日后再怎么“勤奋”也难以弥补。怎么讲?该读书的时候,书还不如现在的奢侈品,奢侈品至少还能看到图片甚至见到实物,而彼时的书不知藏在爪哇国的哪个角落,连个带字的纸片影子都很少见。如我这般对书饥渴的孩子,就成为一棵倒霉的小树苗,在嗷嗷待“水”的年龄偏偏干早无雨,等它歪歪斜斜成年了,明显地“弱不禁风”,无论“体质”还是“风貌”绝对的先天愚弱。这也直接导致我成年后在写作上的“手长衣袖短,不敢下东吴”。
不过,尽管如此,字典阅读已让我成为小村里的阅读冠军。每当语文课到来,我最期盼的就是写作文,零散的阅读,成为我作文课上资“炫技”主壤,让我的作文很快在班里崭露头角,从小学到中学,语文老师多次在课堂上朗读我的作文,写有我名字的作文出现在全校黑板报上,那样的“荣耀”在当时大概与后来的报刊发表相差无几吧,而语文课代表这个“官职”也形成老师对我独有的偏爱,仿佛接续着父亲捧读的画面,给了我无言的勇气和昭示,提示我可能要写点什么。
随着文字的旖旎亦步亦趋,烟萝深处,文学生根。高考后到省城求学,第一次惊讶于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一种建筑物叫“书店”,才知自己与书的世界间隔了多久!从此双脚就像长了眼睛,人也成为书店常客。
工作、成家后,父亲有时跟来居住,每次仍带着一两本用破布包裹的书。此时那些书已经像他的人一样訇然老去,黄旧残破,仿佛分分钟风蚀成尘。他经常倚在床头或沙发,仍是那个固定的捧读姿势,陪伴了我初为人妻人母时的焦头烂额。
尽管所学专业与文学南辕北辙,一种写作的渴望在心中隐秘滋生。从晚报的豆腐块开始了我的“写作”,并不脸红的一摞发表剪报,让我从一名纺织技术人员成为一名党校教师,自认为越来越近地拥抱了文学。
一入烟萝,彳亍而行。
初站党校讲台,没有想象中的紧张,反而赢得一片赞美,以至有一段时间,我竟爱上了“授道解惑”,并准备当作终生职业。
可是,后来的环境如温水煮蛙。在党校时间久了,本以为更靠近文学,哪知身处的气场与文学凛然相悖,使我的“写作”更多处于地下、半地下状态。身边幸福的同事们,可以为唯品会的一张打折券手舞足蹈,也经常为学会了一个广场舞步兴奋一天,每天上午和下午,她们把教室桌椅叠放,腾出一块空地,一个小时的广场舞能让她们如沐春风。她们的美满衬托着我的纠结和痛苦,不觉间我又渐渐回到文学身边。原来,文学是为痛苦预设的,幸福和圆满不需要文学,我的写作,仍在“地下”。
业余写作的这些年,每每参加文联、作协的活动,总被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刺激”着:文联、作协、宣传部、报刊、出版社、广电……凡目力所及,谈及学历时,多为某师范大学中文系;往往主宾相见,“师兄”“师弟”“师姐”“师妹”此起彼伏,让我啧啧生羡。后来扩展到全国的文友、编辑,中文系的“标牌”愈加响亮: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北大中文系也不鲜见。往往这时,心被一次次蛰疼。倘若中文二字再缀以硕士、博士,并且此时的你恰好出现在我面前,我那满身的无地自容你算是逮定了。
太多安慰纷至沓来——“中文系未必写作,太多作家并非出自中文系”之类,表面上只好收下这贴心的善意,心底却依然觉得对方在“站着”说话。我承认安慰背后的真诚,可是每当在写作中遇到文学瓶颈以及基础和阅读的短板,心底的沮丧和低落,岂是一句安慰能够消抵?
写作之前,并未发现这么多的“中文系”啊!我所在的党校,同事的学历专业五花八门:哲学、历史、经济、政治,甚至物理、计算机,而我,纺织专业算是奇葩中的奇葩了。只有身处写作,非中文系这一缺憾立即被N倍放大、显形。缺席中文系,或许对人生的其它侧面并无妨碍,但对于写作,却是永远的痛:自小学起民办教师教错的字词,诸多必读作品的生疏,系统性阅读的盲点,美学、历史、哲学等知识的空白……这一切不断被“中文系”提点、发酵,几欲束戈卷甲。总之,未读中文系的遗憾,在一个涂着浓重文学情怀的人身上有多沉重,即使再设身处地,也并非中文系中人所能体味。
中文,仅仅两个字,已经魅惑无垠。尤其是,你爱的是文学,那就旋即生出太多幻梦与憧憬。在我看来,没有哪个专业能比中文系更蓬勃而诗意了,每天浸润书香,满眼诗情画意,还没走出校门就清晰了自己的诗和远方。读文学作品再也不惧被指“不务正业”,再也无须偷偷地掩在文件下、藏在抽屉里,而是堂而皇之地广而告之——我在读书!每想到这些,心都酥了。
为了接近甚至达成久久盘踞于心底的中文系梦想,我曾试着做过多种努力。比如刚参加工作时买过成套中文系教材自学。当年分配到纺织厂工作,浸淫于纺织技术中,名曰“技术员”,一起分配来的同学都手捧专业书籍解决技术难题,而我包里随身装着的却是中文教材,尴尬与违和交替上演,整个人的拧巴,不知如何投射在他人眼前,自己却兀然默念:现代科技能搬动一座喜马拉雅山,却不能让人心增加一分善良(前苏联科学家语)……
终于,工作两年之后,上级局给各纺织厂提供了赴燕山大学全脱产进修两年的机会,前提是——纺织机械专业。我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入学考试,我们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这时,我鼓足勇气找到组织部,希望改专业——改读中文系。组织部长告诉我,这次进修是“定向”的,回来后都要提拔到中层领导岗位,比如车间主任或科室正副职,“你学中文系,把你放在哪里呢?”我不假思索:“去子弟学校,教语文。”
无疑,我给那位部长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不过他和蔼地答应向上级转达我的诉求。结果,可想而知,毫无余地驳回。我依然不放弃:我自费入学总可以吧。答:并非学费问题。
经历了生活的艰辛,在理想和稻粮面前,无奈选择了后者,却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放弃了那次进修:想到曾经在机械理论课堂上的头疼欲裂,若再去“疼”两年,不禁战栗。
不久,厂里分来一名来自广东某大学的纺织专业女大学生。她是挟着一股咸湿海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明艳张扬的衣妆,明目张胆的“翘班”:今天请假参加模特表演,明天又自费到上海看画展,她的理想是艺术设计。由于她经常请假,厂里多次警告,但鉴于那时纺织专业人才奇缺,我们这批毕业生被当作宝贝。终于有一天,她辞职了,到天津某大学去学她的设计。我和她住在单身宿舍的同一层,彼此房间斜对门,她那离去的背影啪啪地抽我耳光,瞬间让我产生一种奇异的冲动:那一刻,从肉身中飞升出来的另一个我,正朝着不远处的河北师大中文系教室狂奔……
现实还是牵住了梦想的衣角,我让自己无比凄惨地败给了生活。此后的岁月,中文系,一直挂在理想的天幕,比月亮还遥远。
皆因与中文系无缘,导致我几度放弃写作,甚至连阅读也曾疏远。加之迎面而来的现实人生,有一段时间,我不惜对着文学躺平、摆烂,那一刻,类似“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安慰,俨然一副美妙的麻醉剂。
我的写作,还离不开一个遥远的英国作家——毛姆。
20多年前,翻阅一本《世界名著速读手册》,一众名著一滑而过,当《月亮与六便士》这个书名进入视线时,我承认身心为之一动。认真看了简介和名句之类,当时就买了一本读完,震撼是必然的,却也谈不上多么“一见钟情”,然而从此,再读其它书时,思维的某个触点总是被不由自主地拉回《月亮与六便士》,这让我不断重读,加之这时渐渐有了网购,就买来毛姆的传记和《人生的枷锁》《寻欢作乐》《刀锋》等,这时如果再提“钟情”,我已经无力否认了。
当开启我的毛姆阅读,网购带来意外的便利,至今我已拥有九个版本的《毛姆传》,《月亮与六便士》七个版本,每隔一个季度,都会到当当或京东查阅毛姆新译本,于是至今也积累了全部的毛姆作品中译本,并在2017和2024年分别奔赴大溪地和英法等国追寻毛姆的遗迹。
毛姆的阅读与写作成为我的生活常态,我当然明了这位毒舌作家的非同寻常,以及他那不堪的亲情,他生理上的口吃和矮小,他在人群中的自卑和腼腆,他对金钱的锱铢必较……可是他却为读者奉献了一百多部长篇、中短篇以及戏剧、散文随笔等作品,至今他依然不断“涨粉”,正应了他在《月亮与六便士》开篇时的一句话:“艺术中最有趣的就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艺术家赋有独特的性格,尽管他有一千个缺点,我也可以原谅。”
有一点是难以跨越的:尽管自从2016年毛姆作品进入公版,毛姆热席卷全国出版业,他的作品受到空前的追捧不假,但作为籍籍无名的我,所写的关于一个虽受追捧却被定性为二流的毛姆,无论发表还是出版,也是空前的艰难,所以迄今为止,为我出版《毛姆:一只贴满标签的旅行箱》《毛姆VS康德:两杯烈酒》的“鸿图巨基”出版人,以及成都时代出版社和北岳文艺出版社就被我感激涕零。
而这样的写作过程,打着文学的旗号,你必须与社会和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牵连。我承认,自己无论如何清高,也无法做到每天写的东西只给自己看。我可能只是“写”吗?写给谁看呢?我甘于让自己文字终生趴在电脑里不见天日?遥想写作之初,如何将自己写的“捣腾”出去,并未用太多甚至根本没用心思,莽撞着盲投,撞上了一些“知已”,更多的是泥牛入海,报社、刊物、出版社、作协、文联,成为写作必然的绑架物,我想任何一个写作者,只要他想让世界看到自己的文字,都要或远或近、不由自主跳上发表和出版这两驾战车,而这,又是我最致命的短板:社交恐惧和低情商。
这样的自知,让我一直避开职业生涯中的所有仕途,付出了降薪的代价,为的是远离人群,早日拥抱想象中的文学。不知不觉间,自己已成为文学的人质。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的自我剖析足够狠:“如果我置身于一个荒岛上,确切地知道除了我自己的眼睛以外再没有别人能看到我写出来的东西,我很怀疑我还能不能写作下去。”而他设计的男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却向往一个“包围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的小岛”,一个岛上幽僻的山谷,一个人“寂静安闲地生活在那里”,就能“找到我需要的东西了”……
而我,可以吗?显然,我对自己的定力,深深怀疑。
写作着是快乐的,但发表、出版、获奖、排行榜……也衍生出重重苦恼,谁若标榜自己从容不迫,心如止水,离鬼话就不远了。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该退场的时候,失落、不甘如小鼠噬心……有时很丧很丧,只剩下一种苍凉的疲惫和无力感,颓丧,低落,自卑,自我怀疑,身心俱疲,新一轮迷茫,一种严重的避世情结悄悄滋生。
蓦然回首,时写时歇近四十年,隐秘的欢乐和内心的冲突一直相随,哪有纯粹的获得,更多的是长长的跋涉。在这方面,我自愧低能,社恐刻板,缺少幽默感,率直不懂得迂回,我得优雅,我得风趣,还要懂得经营自己,比如书稿选个热点就被抢着出版、获奖,找个文联作协的人员合著一本书就不愁出版,有个京牌靠山作品就很容易“打”出去……可是这些,都是我生命的死结,何况,我并不想让自己焊死在轰隆隆的文学机器上。
正因此,我感谢至今那些从未谋面而一直发表和出版我作品的编辑们,他们从古稀到90后甚至00后,我仅仅在照片里见过他们,大部分甚至连照片也没见过。
并无遗憾的是,我也曾写过相当数量“无愧于时代”的作品,经历这一切之后,我在内心隆重地让自己“回落”:我笔写我心。
记得一位华裔作家把写作比作“红舞鞋”:只要套在脚上,就再也脱不下来,一直舞到死……一位女作家告诉我:“文学真纯美好,但这并不等同于与文学有关的人和事……”我和身边的一些文友往往与现实拉锯,多次喊着“不写啦、不写啦,死都不写啦!”
可是,转过身,痴迷癫狂间,不写才会死。
烟萝深处,文学不死。
2024年9月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