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关注
2025-09-24 20:24

![]()

在中国制造的宏大叙事中,东莞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符号。从“三来一补”的起点,到如今OPPO、vivo、华为等品牌的集聚地,东莞的产业进化路径,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缩影。
6月份,财经作家王千马与吴诗娴合著的新书《“制造”新东莞》出版。该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深入东莞的肌理,试图呈现一座城市如何从“世界工厂”迈向“制造美学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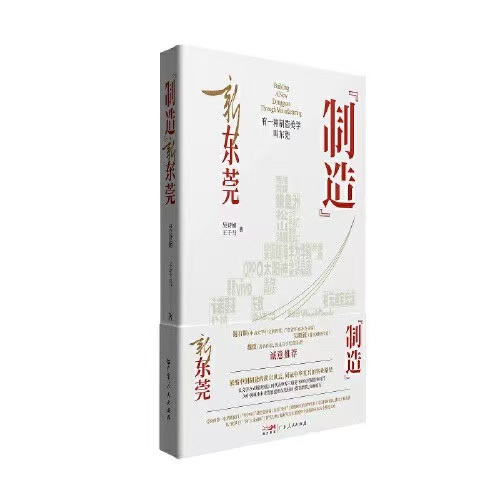
近日,《经济观察报》专访王千马,围绕东莞制造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制造美学”概念展开讨论。
以下为访谈内容。
东莞制造史
经济观察报:你和吴诗娴合作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为何选择以“报告文学”而非纯财经或历史视角来书写东莞制造?
王千马:作为“吾球商业地理”的创始人,我一直着迷于“城市的生长与未来”,自然不会错过对东莞这样一座标志性城市的深入探索。东莞与苏州一样,是中国制造的代表,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路径的一个生动缩影。吴诗娴老师在东莞生活多年,是真正的“东莞通”,对这座城市有深厚的情感与洞察。再加上广东省作协和东莞文联的支持,天时地利人和促成了我们的合作。
我们选择“报告文学”,是希望跳出传统财经写作的刚硬框架,赋予文本更多人文厚度与艺术感染力。因为东莞制造的故事,从来不只是机器、数据和产值的故事,它更关乎人、关乎城市、关乎时代的精神肌理。我们要让读者看见一个多维、真实、有温度的东莞。
经济观察报:在书中,你用“世界工厂”的宏大叙事开篇,却很快切入到具体的企业和人物故事。这种结构设计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千马:我们刻意采用“从宏观带入微观”再“从微观切入宏观”的叙事策略。虽然写的是“东莞制造”,但我们不希望它变成枯燥的产业报告。任何经济现象的背后,都是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具体的选择。因此,这本书以“人”为主轴展开——通过亲历者的声音、真实的企业历程,拼贴出一幅完整且具有生命力的东莞制造图景。
经济观察报:你提到写作是让东莞制造“被看见”。在调研中,你发现哪些价值是被外界传统认知所遮蔽的?
王千马:东莞长期处于广州和深圳的“光环之下”,其独特发展路径常被忽视。很多人对东莞的认知仍停留在“代工基地”“山寨之城”。而《“制造”新东莞》正是要打破这些刻板印象。比如书中写到,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东莞就已开始反思产业“只有星星,没有月亮”的局面。后来引进诺基亚,就是一步极具远见的“破局之举”。尽管诺基亚后来退出,但它为东莞埋下了高端制造与供应链升级的火种。
经济观察报:书中讨论了2008年金融危机等“风暴”。东莞制造展现出怎样的韧性?能否分享一个“转危为机”的案例?
王千马:2008年金融危机对东莞的冲击尤为深刻,但危机也暗藏转机。一批有远见的企业家开始主动求变。比如尹积琪创立品牌“迪宝”,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姚明穿得正是该品牌鞋子;曾凌灿创办“莫失手袋”,从代工走向自主设计与品牌运营。正是这种在危机中自我反思、果断转型的勇气,让东莞制造逐渐积累起产业深度与应变韧性。
经济观察报:在调研中,哪些东莞企业或人物的故事最让你触动?
王千马:最打动的无疑是像李实、王馨、向莉、柳冬妩这样从基层打拼出来的普通人。比如盟大创始人李实,被人以“招工”名义骗到东莞,从保安起步,最终创业成功。王馨和向莉曾是流水线上的打工妹,却通过自学和拼搏,走出流水线,走向管理岗位甚至创业。柳冬妩怀揣诗人梦,走进车间,却用诗歌记录打工生活,最终成为作家。这些人的经历,正是东莞制造最具温度的部分。
从“骨骼”到“神经”的关键一跃
经济观察报:东莞40多年从农业县到制造重镇,你认为最关键的转型节点是什么?
王千马:东莞的转型跨越了几个关键阶段:首先是从农业县转向农村工业化,通过“三来一补”初步建立制造能力;第二个节点是从“只见星星,不见月亮”转向培育现代制造名城;第三个转变是从镇街各自为政走向区域协同发展。而最具决定意义的,是松山湖高新区的设立与发展,它意味着发展逻辑的根本转变: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依靠创新驱动。
经济观察报:从最初承接产业转移的节点,无疑是硬件、厂房、设备等“骨骼”到如今构建自主创新链、供应链的研发、设计、品牌、数据等“神经”,最关键的一跃是什么?
王千马:你所比喻的从“骨骼”到“神经”的跃迁,最关键的一步,正是这座城市实现了从“被动承接”到“主动创新”的意识觉醒和能力构建。它不再满足于只做世界的工厂,而是要成为原创技术的策源地、供应链的控制节点和品牌的高地。
OPPO和vivo的崛起正是这一跃迁的生动体现——它们从早些年的代工生产,逐步走向自主研发、设计甚至定义产品,完成了从“制造”到“智造”的跨越。而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平台,则代表了东莞面向基础研究和前沿创新布局的决心,旨在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它们共同标志着,东莞制造正在深度重塑自己的“神经体系”。
经济观察报:东莞制造经历过“代工贴牌—自主品牌—智能制造”的演进,你如何看待“生存压力”与“创新动力”之间的关系?
王千马:代工贴牌对刚起步的东莞是现实且安全的选择。但随着土地资源紧张、人力成本上升,这种模式难以为继。生存压力成为很多企业走上创新之路的最直接动力。它们意识到,只有做自主品牌,才能掌握定价权;只有投入研发,才能摆脱低端锁定的命运。生存压力与创新动力,在东莞制造的进化中,构成了一对相互催生、彼此成就的推动力。
经济观察报:书中提及诺基亚东莞工厂的兴衰。你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它留下的最大遗产是什么?
王千马:诺基亚的引进是东莞主动寻求产业升级的壮举。它的退出,反而为东莞敲响了更深刻的警钟:产业转型不是一次性的任务,而需要不断迭代、持续突破。诺基亚留下的远不止成熟的产业工人和供应链网络,更宝贵的是一种“居安思危”和“持续进化”的转型意识。
经济观察报:近年来东莞在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崛起,你认为其产业升级背后的核心支撑是什么?
王千马:产业升级的背后是科技,但科技的发展靠人才,而比单项要素更重要的,是生态。松山湖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构建一片“工业雨林”——高校、研发机构、企业、资本、政府形成紧密互动、彼此滋养的关系。政策是“土壤培育者”,人才是“种群”,产业生态提供“气候与环境”。这才是东莞从“制造”走向“创造”的底层动力。
从空白走向空白
经济观察报: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碳中和目标下,东莞制造的最大机遇与风险是什么?
王千马:风险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三重压力:一是产业链迁移的压力,部分低附加值产能向东南亚等地转移,对传统制造环节造成冲击;二是技术竞争的压力,尤其是在中美科技博弈背景下,高度依赖外部技术的领域面临不确定性;三是绿色转型的压力,作为制造大市,如何实现碳中和目标同时保持产业竞争力,是一个系统性的挑战。
但风险往往与机遇并存。对东莞而言,当前也正迎来三大机遇:一是产业链重构下的高端攀升机遇——正如当年从诺基亚的挫折中培育出华为、OPPO、vivo等自主力量一样,当前的外部压力正在倒逼东莞加速核心技术攻关和品牌建设;二是碳中和背景下的新赛道机遇,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正在东莞快速成长,例如氢能产业链、新型储能等已逐步布局;三是数字化智能化的融合机遇,东莞深厚的制造底蕴与数字技术结合,正推动传统工厂转变为“工业互联网+低碳智造”的新型生产体系。我依旧相信东莞,一方面是相信其向死而生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是相信它深度嵌入世界产业链所形成的独特优势。
经济观察报: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东莞制造的精神内核”,你会如何描述?
王千马:正如我这本书中所前后呼应的那样,就是:从空白走向空白。
第一个“空白”,可以理解为一种“零”的状态——早期的东莞夹在广深之间,作为农业县,既缺乏大城市的资源集聚,又面临人才、资本的虹吸效应,就像珠三角夜晚的灯光图:广深璀璨夺目,而东莞却显得黯淡。这种“空白”,是经济洼地的象征,是未被定义的原始状态。
但换个角度看,这种“空白”又像中国画里的“留白”——它不是空洞,而是充满可能性的未完成状态。东莞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它没有被既定模式束缚,反而在广深的夹缝中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它通过农村工业化、通过“世界工厂”的崛起,在原本的“空白”上无中生有,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
而第二个“空白”,则是对未来的隐喻。我不希望东莞被过去的成功固化,而是期待它保持“空白”的开放姿态——不再是虚无的零,而是能包容创新、多元与变革的“大有”。就像书末写到的:“空白的五颜六色,沉默的震耳欲聋。”未来的东莞,应该是一片能孕育新事物、新文化的沃土,既有制造业根基的沉稳,又有破界生长的活力。
总之,这句话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隐喻——东莞制造的精神内核,就是一种在不确定性中创造确定性、在无人地带构建新生态的开拓者意志。
经济观察报:对年轻一代理解制造业、投身制造业,你有何建议?
王千马:无实体不未来。制造业始终是一国一城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年轻人应当意识到,制造业不是“夕阳产业”,而是支撑中国走向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内容。我送他们两句话:“勇于开新柱”和“也要老树发新花”。今天的制造,是人机协同、数据驱动、创意落地的创造性活动。制造,可以很酷,也应当很酷。
东莞制造美学
经济观察报:东莞要完成城市品牌跃迁,最需要补上的一课是什么?“制造美学”能否成为新标签?
王千马:东莞仍需在三个方面发力:强化工业设计与研发能力;构建文化软实力;推进城市空间更新。“制造美学”可以成为串联这些维度的关键标签,帮助东莞跳出“世界工厂”的传统认知,转向“智造之美、生态之美、人文之美”的新形象。
经济观察报:东莞的“产城融合”实践如何体现制造美学的空间表达?
王千马:松山湖和滨海湾新区不仅是产业园,更是以“人”为中心、以“创新”为脉络的新型城市空间。松山湖的华为欧洲小镇与湖光山色交融,滨海湾通过TOD模式将产业功能与生态廊道结合。这些实践重构了一种新的工业城市形态:产业、城市、自然多维融合。
经济观察报:东莞经验对中国其他制造业城市是否有借鉴意义?
王千马:东莞最大的启示是“实体立市”与“与时俱进”。但每个城市条件不同,未必有东莞的区位优势。可借鉴的是其“无中生有、敢为人先”的制度创新精神和市场敏感度。东莞的真正启示在于:城市能否持续进化,不在于起点,而在于是否保有重塑自我的意愿和能力。
(王千马系吾球商业地理创始人,著有《城市战争》《新制造时代》)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