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源:IC Photo)
马向阳/文
小说大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读的,一种则可以用来把玩。事实上,从来没有一种游戏能比文字游戏(一种能指符号的游戏)更令人着迷的了。在语言(能指符号)建构的迷宫里玩弄捉迷藏的游戏,向来是诸多伟大作家乐此不疲、精心营构的“盛事伟业”——博尔赫斯的小说《小径分叉的花园》里层层叠叠嵌套的时空迷宫追踪,曹雪芹笔下曾经埋葬青春无数、白茫茫大地一片的大观园情感考古纪录,以及艾略特诗歌《荒原》中如巨碑悚然的繁复隐喻象征,都是叹为观止的符号游戏。
《微物之神》就是这样一部“另类小说”,它精心构造的文字迷宫既让人烧脑,又令人沉醉其间,作家余华和戴锦华教授都特别推荐过印度裔作家洛伊(ArundhatiRoy)的这部小说,甚至每过几年就要拿出来再重新读一遍。《微物之神》通过一对双胞胎孩子艾斯沙和瑞海儿的视角,透过孩子眼中密密麻麻的、各种不起眼的微物(smallthings)所代表的各种意象和象征,比如他们的表姐苏菲默儿躺在棺材里被掩埋之际棺材里那只垂死的蜜蜂;他们的祖父帕帕奇最忘不了那一只灰色、多毛、背部有特别密的簇毛的象征着恶性鬼魂的蛾子;还有摇摇晃晃地走在一条满是横冲直闯的车子的公路上的、最后被压烂的青蛙,如此等等……这些隐喻大都寄寓了一个前现代印度家族生活的恐惧和失落、绝望和爱情、抗争以及死亡。
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两个孩子的母亲阿慕最后不惜用生命的代价去争取“活着的机会”——她走向“贱民”木匠维鲁沙的致命一步,犹如飞蛾扑火一般。这个梦中反复出现的男人是她的“失落之神、微物之神、鸡皮疙瘩和突然微笑的神”,小说最后一章的大揭秘,巧妙回应了小说开头第一章的迷思。和侦探小说不同的是,洛伊这部悲剧小说哀而不怨、怨而不伤,在密密麻麻、层层铺垫和反复出现的种种意象编织中,阿慕们甚至都很难用“活过”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在帝国阴影和历史账簿中,文章中着墨众多的几位女性都只是历史中苍白的“微物”,她们活着是小人物,死去也只是历史上重复出现的、了无新意的不重要的小东西和神秘幽灵罢了。
回旋意象:历史的回声
作为一部神奇的回旋小说,《微物之神》的第一章“天堂果菜腌制厂”到最后的第二十一章“生存的代价”,几乎每一章的故事既相互嵌套在一起,在时间的线性叙事中又充满过去和未来的交织,有点像中国诗歌中的“回文体”结构,这样的一种精心安排,不但故事情节充满了各种遐想迷思,更让人感受到一唱三叹、意味难尽的悠长余味,不能不说,这是一部需要反复阅读、咂味、摩挲的,蕴藏着奇特叙事结构和耐人寻味意象的巧构小说。
在小说第一章“天堂果菜腌制厂”里,主人公阿慕的两个孩子——成年后的兄妹艾斯沙和瑞海儿23年后再一次在阿耶门连的祖屋相逢,一个是从他们的父亲那里被送回来,另一个则是从美国远道而回,故乡重逢使兄妹两个想起了23年前他们的表姐苏菲默尔从伦敦来阿耶门连度假并客死他乡的奇怪故事。这23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的表姐为何很快就客死在阿耶门连?两条故事层层交错,相互缠绕,最后牵扯出一件更加隐藏的悲惨情爱故事——他们的母亲阿慕和木匠(贱民)维鲁沙的相爱,因为逾越了“爱的法律”而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故事的套层结构,由此一步步地慢慢展开。两个孩子的表姐苏菲默尔究竟因何而死?他们的母亲阿慕在参加表姐苏菲默尔葬礼后去警察局到底说出了什么秘密?在经历过那“恐怖”的一天之后,为什么此后哥哥艾斯沙必须立刻被送回父亲身边?作家罗伊开篇紧紧抓住读者好奇心的同时,却同时扔给读者一堆“大火发生之后满屋子的残骸”,接下来以阿慕为主人公的这部印度人的家族史在余下的20章里,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一个意象接着一个意象、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徐徐展开,作家不仅在验证我们的耐心,更希望我们从那些“被烧焦的时钟、燃烧过的相片和焦黑的家具”中发掘出“历史的真相”来。
这些残忍的真相被隐藏在闪烁不定的意象里。作者擅长用回旋、致密、涡旋感的语言编织出种种繁复而富有意味的意象,这些意象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这种反复使用的电影“闪回”手段,进一步临摹出一种旋涡般的时间;让读者在小说所建构的时间迷宫里,发现独特的幽灵萦绕的恐怖氛围——即主人公阿慕在每个“恐怖”时刻都像是历史的幽灵。尤其是在反抗之前,她们只是属于历史秩序的固有部分,好像从来不曾“活过”一样。
以“蛾”和“爱的律法”两个反复出现的意象为例。在第二章“帕帕奇的蛾”里,主人公阿慕的父亲帕帕奇曾经是一位大英帝国昆虫学家,依靠大英帝国秩序的庇荫,他一路官运亨通,退休时已经当上了普萨学院动物研究院的院长。但是当印度独立、英国人离去后,他头上的帝国光环开始变得黯淡无光,很快遭遇了他生命中最大的挫败——他所发现的蛾并没有以他的名字而命名。
在小说原文中,这只蛾分明是“帝国魅影与后殖民文化”的隐喻象征,帕帕奇的个人命运最大挫败以一只蛾来象征,甚至成为他后来“郁郁寡欢和突然发怒的原因”,“它恶心的灵魂——灰色、多毛、背部有着特别密的簇毛,纠缠过他住过的每一栋屋子,它折磨他。折磨他的孩子,以及他孩子的孩子”。
在小说中,这只蛾反反复复地出现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中,但其寓意分明只指向一处,它鲜明地嘲讽了帝国秩序的垂死和衰亡,不管它此前如何狰狞和丑恶,而且这种帝国魅影连同其殖民文化,已经深深植根在这个印度家族的每一个分子的每一个时刻,根本就无法拂去。
至于“爱的律法”,则是一部规定“谁应该被爱、如何被爱以及人可以得到多少爱”的律法,在小说中,它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及,隐喻了现代印度人生活中宗主国、种姓制和父权制依然活跃的种种恐怖影响力和僵化的传统制度。阿慕的父亲帕帕奇动辄就喜欢用黄铜花瓶去殴打他的妻子,在女儿阿慕看来,“人类只是习惯的动物”,“只要看看四周,就会发现,拿黄铜花瓶打人是这类事物当中最不会令人大惊小怪的一种”。在阿慕家族的三代女性代表中,她的母亲玛玛奇只能默默地承受家庭暴力;阿慕早年草率所嫁的老公是一个加尔各答的茶庄助理,不但说谎成性、酗酒度日,甚至劝说妻子接受他的英籍经理的提议,用她的身体去换回她丈夫的工作,遭妻子拒绝后反而殴打她;从小就生活在和平恐怖中的瑞海儿甚至害怕婚姻,结婚不久就离婚了。
在瑞海儿看来,一旦打破那些“使祖母成为祖母、舅舅成为舅舅、母亲成为母亲、表姐成为表姐”律法,闯入禁区,就成了最糟糕的逾越者,随之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部超时空、无边界的律法当然尤其相当荒唐的另一面:阿慕的哥哥恰克也与他的前妻玛格丽特离了婚,当阿慕因为离婚成为一个可耻者时,这位玛格丽特因为是英国人,这一特殊身份在印度足以抵消她作为女人的全部罪过,当阿慕遇上了贱民维鲁沙、迸发了爱的火花而受到无情诛杀之时,阿慕的哥哥恰克喜欢招惹工厂女工,却被视为一种正常的生理需要,他的母亲玛玛奇甚至在她儿子的房间另开了一扇门,专供这些低级女工们方便出入。
从双胞胎兄妹的表姐苏菲默儿来到阿耶门连的那一天开始,表面上看,“事情可以在一日之内发生变化,而数十个小时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可是作者笔锋一转,“事实上这件事开始于数千年前,开始于马克思主义论者到来之前;开始于英军攻下马拉巴尔之前……甚至可以说,这件事开始于基督教乘船到来,并且像茶包中的茶那样渗入喀拉拉之前”,当然也是“开始于爱的律法被订立之时”。
在小说叙述中,作家大量使用简洁的名词和极端简约的不规范动词,并使用大量回旋的长句、大量的罗列来排列组合成各种光怪陆离的意象,这些意象和文字形成了流水般的旋涡,洛伊向读者清晰地展现了23年后重逢的这对孪生兄妹和这座印度南方小镇里的老屋里曾经见证的一切——历史和现实如何相互切换、代替和纠缠在一起,以及阿慕家族中的每一个生命都曾经被时间深处的历史幽灵所塑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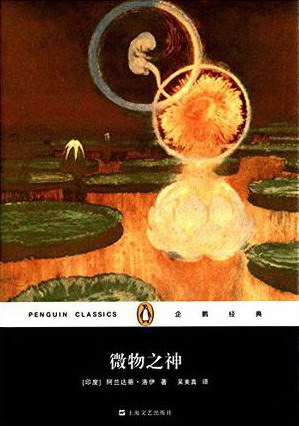
《微物之神》
作者: [印度] 阿兰达蒂·洛伊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译者: 吴美真
出版年: 2014-5
幽暗生灵:帝国的秩序
以诗性的语言来展现帝国秩序的残酷,戴锦华教授曾经激赏过《微物之神》的独特叙事美学——当诗性的语言和高度致密的文字结合在一起,每一组文字成为如同钻石一般的多面体,每一个形态各异的截面,都折射出历史殿堂深处那些幽暗的创伤。这不仅对读者的阅读构成挑战,也让读者在这部小说里看到了文字和语言可能产生的革命性、创造性的作用。
以第二十一章“生存的代价”为例,小说在铺垫主人公阿慕和木匠维鲁沙相爱时这一高潮段落时,有这样一段白描:
“仓皇疾行,全世界已经消失了。
正要去工作的白蚁。
正要回家的瓢虫。
正要掘洞穴避开亮光的白色甲虫。
拿着白木小提琴的白色蚱蜢。
悲伤的白色音乐。
这一切都消失了。”
这样的一连串高致密名词,不仅把读者带到了阿慕和木匠维鲁沙偷偷约会时有质感的物质场景,更铺垫了一种美好而又悲伤的故事基调。洛伊在这部小说中并没有讲述什么惊世骇俗的故事情节,甚至只有一个老套的爱情故事和家长里短的家族日常生活场景,可是,一旦作家改变了它的讲述方式——以全新的、动人的、直接的方式去触碰你的心灵时,这种唯美语言下掩盖的残酷真相,就会像利刃一样刺伤你的心灵。
在第十八章“历史之屋”中,小说的残酷主题更多了进一步的诗性展示。“历史之屋”是阿慕和贱民维鲁沙的约会之地,就像是一位沉默的历史见证人,在阿慕和贱民维鲁沙之前,这里曾经是一个卡利塞普(意为本土化的白人)的房产,他的爱人原本是一个本地男孩,男孩被父母带走后,他也自杀了,这里由此成为弃屋。卡利塞普曾经是一个双重的逾越者,一只脚踏过了宗主和被殖民者的界限,另一只脚则将爱跨越了性别。当警察们在“历史之屋”将贱民维鲁沙打得奄奄一息时,作者用极其冷峻的文字写道:“这些人只是历史的追随者,被派去结清账目,向那些违反其律法的人收取他们应该付出非代价。一种原始但完全非人性的感情驱使着他们,一种从刚生成的、未被承认的恐惧生出的蔑视感驱使着他们——文明对于自然的恐惧,男人对于女人的恐惧,权力对于没有权力的恐惧”。
为了维护帝国秩序的一致性,权力自身成为唯一合法的“神性”。对于阿慕和贱民维鲁沙这样生活在帝国秩序的幽暗生灵而言,他们只不过是权力之下的卑贱“微物”(smallthings)。
《微物之神》的故事内核源于洛伊小时候母亲讲给她的乡间传闻:一个上层的叙利亚基督教离婚女人与贱民木匠跨越种姓、阶级的悲伤爱情故事。在洛伊生活过的印度喀拉拉邦的家乡,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以诗性文字描写残酷,用语言碎片来拼凑暴力,以幽灵般记忆来记录帝国秩序,《微物之神》就是这样一部能带给读者沉浸体验的迷宫小说,它值得你在一个冬日慵懒的下午阳光里,捧着它在膝间,看生命之流,就像是咀嚼一块味道复杂的奶酪饼干。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