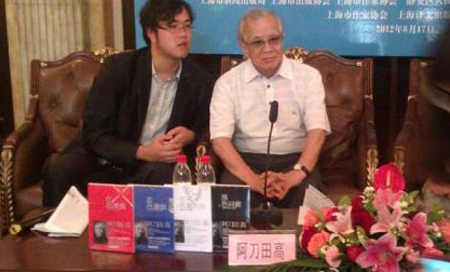
对谈会中,阿刀田高静静听口译翻译对话内容 侯思铭/摄
阿刀田高:的确如莫言先生刚才说的,今天这个对谈的主题,是由我提出来的,“小说为而何而存在”。其实我个人作为小说家,已经写了40年,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是在我脑子里面一直有的一个问题。小说为什么而存在呢?当然作为小说家我也会考虑,为什么存在呢?我为什么写呢?所以今天有这么一个主题来和莫言先生聊,非常的高兴!
小的时候我就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一个少年,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读书,也读了非常多的小说。当时其实我并没有过多地想,没有什么目的,完全就是一个纯粹的爱好,所以读了很多很多,包括我后来在大学的时候,也选择了跟文学相关的学科进行学习。但是当我成为一个作家,开始写小说了以后,我也会一直想到这么一个问题----读小说可能是完全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那么写小说又是为了什么呢?把自己写的东西,在社会上发表,这么一个发表小说的行为,里面到底有什么深层的意义呢?从这时候,我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应该说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之后,就到处找,看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书籍或者是文章,关于为什么要写小说,为什么要作文学创作。那时觉得非常有意思,小说是什么?小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样的文章,其实在世界上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国家都有这样的一些书或文章。但是为什么写小说,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我找来找去都没有找到答案。我不知道在座的大家对这个是不是了解。其实我第一次读到为什么要写小说以及文学存在价值的文章,其实是非常著名的中国的伟人毛泽东70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早接触到的是是这样一篇文章。
我读到毛泽东的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的理解是,中国的这位伟人提出的,文艺创作和文学创作,是要为革命作贡献,为革命服务的。它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政治的立场和政治目的,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鲜明主张。当然我个人不能说是完全同意的,如果这么说的话,摆在这里的我的四本书就没有任何的存在价值。像大家都知道的日本的大作家渡边纯一,他的作品也可能没有存在的价值了。甚至可以说,现在世界上有的2/3的作品可能都没有存在的价值。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因为这是我读到的第一个,将文学做了一个非常明确定义的文章。在这个方面,我也想听听莫言先生的意见。
莫言:毫无疑问涉及到一个敏感的问题----毛主席在延安的一个讲话。
首先,我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历史的文献,它的产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也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当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带着很大的历史的局限性。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对它进行弘扬,有两个角度:一是站在今天的立场,用今天的观点来对它进行研究,进行定性;另外一个就是回到历史的角度,站在历史的这种角度上来对这个文字进行研究进行探索。从这样两个不同的角度,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论。
确实,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当代文学,很多前辈作家,是主动的、自觉的把“讲话”作为自己写作的指导方针。但是到了80年代,我们这批作家开始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虽然历史文献有局限性,但我们还是从中吸取了一些合理的东西。比如说要深入中国,了解中国,要跟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从今天来,我个人认为这是它的合理性。
但是我们也看到他过分强调的阶级和政治意识,这影响了作家写作的价值。我的写作之所以在80年代形成一种新的气象,就是因为我的写作突破了讲话的局限。在80年代初期,我曾提出了一个口号,“要把好人当坏人写,要把坏人当好人写,要把所有的人要当作人来写”。在我们过去的作品里面,好人是绝对的好,坏人是绝对的坏,好人和坏人之间不可调和,好人和坏人之间人性上毫无共通之处,我觉得我的创作突破了这个障碍,我的创作出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新的声音,这也是我作为一个作家,能在80年代的中国文坛站住脚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这也是我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认识。
阿刀田高:首先我要非常感谢莫言先生对我这么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作了一个真诚的答复。
回到我个人的文学艺术创作为什么存在的探索方面来说,刚才我说的第一接触的是毛泽东的一个文献,我个人也非常理解他作为一个伟人,中国的一个领导者、政治家,在这么一个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面,作这样的一个讲话,一定是有他的现实意义,我个人也是非常理解的。
这之后,在我个人的文学创作的探索上,我接触到一个日本的作家前辈,他叫伊藤正(音译),这位老作家写过《艺术是为什么而存在》这样一本书,这本书现在在日本,是很多作家,艺术研究方面比较有名的一个作品。在这里他提出了,应该说是和当时中国的伟人毛泽东完全不同的一个观点。他觉得艺术是要为个体的存在,每一个个体的存在意义做一种帮助的价值。
的确全人类的幸福,社会的整体幸福固然是文学存在的一个价值所在。但是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幸福的,在一个社会当中,一定是有少许的阴暗面,或者说关系到每一个个体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悲伤,一些个人的烦恼。很多烦恼,可能如果是个体,他自己在自己的心里说的话,这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阴暗的部分。打比方说日本的大作家渡边淳一,他会经常写一些不伦爱,这样的题材,相信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在一个法律限定的婚姻制度下面,这些都是非常不道德德行为。但是相关到个体的时候,这的确是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非常有份量的一部分体验。可能当时我读到伊藤正的书里面,学到我们的文学是要为这样的一些,某种意义上是不幸的人而存在的。我个人对这样的作品是非常感动的。它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就是感受到了文学、文艺的存在价值。
这是我刚才说到的伊藤正的论点,我个人觉得跟刚才莫言先生的一些观点也是有相同之处的,您觉得怎么样呢?
莫言:每个作家,可能具体了解他熟悉的一个小圈子,或者是写他自己内心的感受,生活经验,亲身经历,这都不妨碍作家写出好的作品。因为创作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劳动,创作最宝贵的本质就是个性的表现,个人情感的流露,个人风格的体现。所以这种个人性跟这种人民性,个体跟群体的写作过程,是一种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只能具体到每一个作家来分析。刚才阿刀田高先生提到的渡边淳一,我也看过他写的《失落园》,也看过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这样的小说按道理说,从社会公认的价值和道德来讲,主人公是有背道德的,他跟有夫之妇偷情,然后再自杀。无论如何也不能鼓励他们为情而自杀,我觉得无论哪个阶层的人,都是不能容忍这种行为的。但作为一部文本,一部小说,又具有它的认识价值。有的读者从里面看到了偷情,有的读者从里面读到了绝望,也有的读者从里面读到了人的精神的苦闷,尤其是中年知识分子、中年男性的这种精神痛苦。
他的作品我也看了很多,所以作为文学作品存在有他的认识价值,也有他的社会意义。但是用道德的标准来衡量,尤其是用这种传统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我想这部作品会遭很多批评。所以我想不仅仅在渡边纯一的作品里,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以及中国的古代文学里面也,有这样的文学作品。我们有一部著名的《金瓶梅》,这部小说里面,可能,大量的肉体性的描写历来有很多的批评,但是也有很多的人对它持肯定的态度。这部小说尽管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但是它作为一部著名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据了不可撼动的地位。
所以我想世界各国的文学都有它的特殊性,有它的个性,但还有一种共性存在的。无论日本作家的作品还是中国作家的作品,通过翻译都可以阅读,都可以被打动,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些作品里面,表现了人类的情感的共鸣的特征。这是我的粗浅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