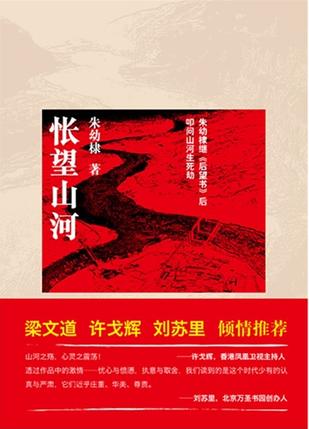马国川:谢谢各位朋友,今天天气不太好,而且因为今天搞马拉松,很多地方交通管制。大家到这里来肯定不太容易,我有一个朋友是中经报记者。曾经做调查,北京一年的交通管制七千次,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二十次。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个当过委员长的,在全国常委会里面。有一次他就说,你们老是说北京堵车,我觉得不堵啊,我每次到走长安街都很舒畅啊。你们以后应该实地调查,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我们来开始比较沉重的话题。《怅望山河》这本书我是周三上午拿到的,到晚上就读完了。读完了之后,非常感慨,文笔非常好,但有一个缺点,看了之后心情特别沉重。真的是特别沉重,就没想到,今天的中国,我们在北京,有时候我做记者可能走的地方多一点,周围朋友可能也走了很多地方,我们走很多地方没有这么深入的去探讨这个国家这么多年来山河如此巨大的一种变迁,而这种变迁,不是按照我们所想象的,向一个更美好的方向发展,而是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发展。大江大河断流,山川断裂等等,这一切问题这本书里面都有反映。
我想是不是首先先请朱老师先谈一谈他到底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是怎么写这本书的?
朱幼棣:因为我写这本书,前后时间经历了五年之久。五年以前,当时出了一个《后望书》,讲到城市的文化遗产、城市风格和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讲到了一些江河水利的问题,是和江河以及跟工程建设有关的。但是当时写的比较匆忙,有一些话还没有说完,一些重要的工程重要的关键字也没有说完。我记得当时跟王军在书店做节目,就有人提出来,说我怎么对长江三峡这么重大的问题都没说。我说我当时已经开始接触了那部分,那时候还没有进入后三峡时期,而且后三峡时期还没有到。很多这东西看的不是很清楚。但《后望书》的最后一节已经讲到了长江三峡问题,我就开始准备写这本书。
这本书准备过程正好碰到了汶川地震,汶川地震应该说是一场我们的重大灾难。汶川地震以前,我正好考察和调查世界文化遗址,也到过都江堰的一些地方。那个时候工程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地步。当时提到了岷江水电,岷江河流都完全干涸了,那时我就想,是不是跟地震有关,当然是可能是一个大体构造的变化。就开始研究地震问题,地震虽然有多种原因造成,但是人为的工程因素也不能够完全排除。
当时我就写了一个关于汶川地震的地质方面的思考,到底我们的地震,也是一个山脊平衡被打破了。这个突发地震有多种原因,有自然的因素,有月亮的因素,还有可能有工程的因素,都不能够排除。我有一个特殊情况,年轻的时候搞过地质。二十几岁的时候在矿山做技术员,看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地质的书。后来我到新华社做记者,跟王军同事,我也是是国家荣誉地质队员,这方面也低调。然后就开始深入就讲、写地震的,比如地震我们应该注意什么,特别是工程建设重大工程建设怎么能够保护我们山区的平衡,使我们江河和山体不受破坏。这就写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写了《大国医改》,把中间断了有一年多时间。
既然讲江河问题,那主要的江河应该有。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究竟是水灾,还是洪灾还是旱灾?我们江河面临着什么?应该说,北方的江河面临的主要的问题是断流和枯竭;中部地区和南方河流主要是污染,而且地下水不能饮用。这样我们就从一个宏观层面,考虑到研究我们主要江河这个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一些变化,这跟我们工程建设,我们治理的指导思想有关。为什么现在海河完全断流?天津原来是一个河口、港口城市,现在天津没有港,海河不能通航,都是近五十年来发生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因为五十年就是两倍人的时间,我们现在刚生下来就认为城市就是高楼大厦,城市就是现在我们的就这个情况,现在孩子觉得河流本来就没有水。这个北京的永定河就是没有水,北京就没有河流。但实际上,历史不是这样的,是我们半个世纪以来,一步一步造成的一个江河、这个山川面貌的一种变化,我想探讨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上,我毕竟不是专业人士,可能研究的有些肤浅,但我想宏观把握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以后需要一些有志于此的人,能够在我们国家宏观层面上来统筹考虑这个东西的变化。十八大里面提到一个是“美丽中国”,把生态文明列入到我们五大建设的总体规划里面去。我多讲两句,这个“生态文明”提得非常正确。我记得前两年有一次国家环保局的人叫生态文明,还有什么城市文明,社区文明、企业文明,都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区分这些文明?我当时就提出,这个文明有两个坐标系:一个是横向的,包括社会、社区、职业、农业问题,道德文明,这个是横向文明;另一个是纵向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手工业文明,还有工业文明,因为工业文明造成了环境和身边的破坏。工业文明的后期就提了一个生态文明,这是一个纵向的事。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十二五”,新一届提到2020年翻两翻,而且标志着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后城市化社会,有些破坏是不可逆转的。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国内提的就是科学发展观也好,我想一个人的科学觉醒是很重要的,这个就跟我们民族觉醒政治觉醒一样,谢谢!
马国川:谢谢朱老师!朱老师讲的很好,我觉得刚才大家注意到,朱老师后来用了一些政治语言。他原来在山西省委办公厅当过副主任,后来到国务院研究室当过司长。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讲到08年温家宝总理去哈佛大学那篇演讲稿,就有朱老师,他当时参与了撰写,是不是您写的?
朱幼棣:我只是参与参与。
马国川:那个演讲稿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刚刚朱老师讲到,就是他的思考一开始是地震,后来是山河的变迁,我看这本书之后对我触动比较大的也可能在座的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他第五章讲的一个问题----北京的水危机,题目是《北京水危机背后》,我看了之后感到很震撼。书里面讲到,其实在清朝的时候,昆明湖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水利工程,而它这个水利工程做得非常好,非常完美。不但解决了北京的水利、供水问题,也解决了灾害----山上下来水的灾害问题。可是后来我们搞了官厅水库,现在水库的问题出来了,水库本身没多少水,下游枯竭。我的问题是提给朱老师和王老师的,就北京的水危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自然原因还是人为的原因,有没有解?朱老师你先来!
朱幼棣:这个是关于北京的,王军老师更有依据,待会请他讲一些更加深刻的。我讲的就是从一些宏观的角度来说的,北京城现在没有一个完整的水系,这是北京最致命的问题。北京没有地表的河流,地表的河流包括永定河,基本上都是断流的。这个是我们解放后,对北京造成最大的一个50年最大深刻的变化,北京永定河和潮白河都是北京的母亲河。解放后,我们第一个水库就是官厅水库。当时设计的库容是40多亿立方米,40多亿立方米就是基本上把永定河的年平均水量的百分之七八十放到官厅水库里,建一个水库就能够解决问题,结果下游一片,上游包括山西境内,包括河北境内,包括内蒙境内,修了很多很多。其中大同的叫做册田水库。控制了永定河流域的40%。你下游建了一个大的,上面又建了一个大的,这个永定河自建立以来一直没有装满水。只有几亿方米。等于修的一个大棚,只有一个小管子里面有水,而且层层拦截。
兴修水利是一个政治化的行动,而且没有全流域统筹的考虑。不但造成了水力资源的大量浪费,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下游一点水都没有,包括卢沟桥下面也没有水了。现在据说北京要花一百多亿打造景观河,就永定河那么这个景观河就不是河了,就是湖,而且没有水,这使北京的地下水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北京应该是城区有湖、有水的,现在水面搬家,湖泊搬家,搬到长城以外居庸关以外的官厅和密云去了。那地方风光不错,有草原,有湖有水,城里却没湖没水,地下水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现在北京70%还是用的地下水,不是用密云水库的水,那么大的水面白白的在蒸发。北京也没有搞一个完整的水系,一下了雨都进了下水管道,下水管道应该跟河流应该分开,地表水还可以再利用的,结果全部进入到地下管道里面去,跟污水混在一起,这样我们的水系跟给排水系统是混在一起混乱了,这可能是北京市整个规划设计上的一个问题,包括护城河什么的都没有了。
我们现在仅有的几个湖,就是元朝设计的,包括中南海、北海,都是郭守敬跟刘秉中设计的。解放后我们还没有搞新的湖,除了亚运会鸟巢那个地方以外。所以要重新恢复北京市的水系,要保护最低的生态的水量和流量,从这个方面来考虑我们北京市的一些规划,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包括调水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想这个王军会说的更好。下面请王军老师!
王军:这个先说几句向朱老师致敬的话,因为朱老师是我在新华社非常敬重的前辈,也是对我进行最高启蒙的前辈。那个时候朱老师还不认识我,我91年到新华社工作的。我看朱老师这本书,还说那会经常写什么城市性的报道,就是长高了长大了,就不懂,一窃不通。那时候写了很多错误的文字。其实我后来写点书,也是自我的觉醒。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朱老师给我很大的帮助,刚才还跟朱老师谈说我看他写的关于北京的这个很多大遗址保护的文章,那时候心里面一下子豁然开朗。然后就说元大都这个遗址还在,看了之后心里面咯噔一下,你看元大都那个时候你看马可波罗,那么震撼,看他的记录里,就知道元大都整个遗址的状况是什么样的。这个对我心里面是有很多的启发。
那会,朱老师很多的文章我都看,然后后来就看他的《后望书》,看了之后也是很震撼。我回忆很深的就是官厅水库,因为南水北调。这个跟北京水有关系,那个时候要继续加高大坝,要翻天。实际上永乐皇帝干了两个大事,一个是修紫禁城,一个是修武当山。那么这两个大事,在解放之后,都遇到了大麻烦。比如说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制定了要改造故宫的计划,在63年做出完全拆除的计划,这是永乐皇帝的一个大工程。还有一个就是武当山,就是丹江口水库,把下面一百多个那么重要的建筑,一点措施都没有的,完全给淹掉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去丹江口水库,因为那个时候要南水北调,我知道那个故事我去采。后来我在看朱老师的书,就写到这些老百姓被搬到青海,我看了之后真的是痛苦。
就这些人,都是一生只能过一次,这些人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工程,他们的这一生就被毁掉了。而且别人一点都不觉得可惜,我看到老师的文字后内心里是非常痛。我在看这本书也是,我就觉得这本书说的一切一切的东西都是一个道德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就要把我们的大好河山为了我们所谓的利益,就要把后人的权利全给提前透支。
马国川:有一个说法,说是牺牲历代人的利益,为了后代,更好更好,还有这种说法。
王军:因为我后来工作的分工,写的城市的建设,这涉及到人文环境的问题,也造成很多的经济自然环境的问题,实际上这两个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后代人的责任,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看你这本书写的册田水库,03年那个时候北京放水,那个时候北京已经干的不得了了。那个时候我正好是陪梁先生,他是刚刚生病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就觉得他是搞环境保护,他很抑郁。我记得我那时候《城记》写完了后就送给他,他在我面前谈的时候就落眼泪。他也说,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环保,呼吁那么多事情,环境保护是越来越差了,那还需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这个是很痛苦,后来我记得有两次聊天说,我就觉得他是搞环保的,就是老百姓一跑到北京来上访了,都把他当政府部门来对待。
他老人家就成天接受这些事情,他只有一颗良心啊,还有别的什么吗?包括里面写的好多的移民,就找他,你说梁先生他能干什么呢,所以他也就是找找我们的记者。看我们这帮记者能不能写点文章呼吁呼吁,帮帮那些老百姓。他很痛苦,梁先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我们这代人是赶不上了,你们怎么办呀?我们很快就过世了,你说中国以后一定人口大爆炸,环境大爆炸,到那个时候,国在山河破,可能是国破山河也破,都不好说了。
后来我那个师傅说我陪你出去散心。他说我还没有看过唐代的那个南唐史。比梁思成和林徽因,发现的那个唐代的还要早,早几十年,那我就说我陪你去,去山西的五台。那次就开着车陪他去看,他看了之后就心情非常好。缓解了他的心情,他那个时候有知道册田水库这个事,就一放水就往北京流。结果没流到北京,这个就大地太干渴了就全部陷下去了。
朱幼棣:因为这个桑干河的上游。水利部门发明了一个词叫做调水。你上游往下游放水怎么叫做调水呢?
王军:这个就是面临大自然的一个态度,这个就是一切都是人工化。你说好象是很计划,其实根本没计划。比如说官厅水库,我是这刚说回到北京一个话题,我是十多年前我和一个同事一块去调查的官厅水库。因为那个时候贾庆林在北京当市委书记,他也说希望把这个非常紧张的一个水流问题。因为当时北京是发了一次大洪水,结果是把密云水库全给装满了。后来我记得是郭金农当书记。他高兴坏了,他说本届政府吃水的问题无忧了。这个吃到贾庆林当书记的时候就开始遭遇这个事了,就希望能把官厅水库给用起来。然后我们又做一个调查,就发现那个里面全是污水,全部是张家口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上面是几百个水库,这个书里面有详细的数字,还是我记得有五百多个水库。把张家口算上河北境内就有二百多个水库,就全给截了,截到张家口那,往下流就没有什么自然的径流了。所以大家到康熙草原去玩,千万别摸那个水啊,那个水是不能摸的。那个水脏的不得了。然后有时候像北京城西边,像石景山、门头沟那边,有时候喝水困难,他们还偷偷的放点那个水。让他沉到地下去。然后再通过这个净化,然后在从地下水在抽出来,那个水都是很成问题的。
所以我就觉得,当然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我就会想到那会毛主席。昨天在北大给同学讲课让同学们分享这个故事,就是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肖像往那一看全部是烟囱。他说从天安门城楼往南边一看全是烟囱,当时梁思成就不能理解,就说中国那么大,为什么要在城框框里面搞工业呢。其实毛主席说这个话他是有想法的。就那种苏联专家来北京搞规划,制订规划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莫斯科我们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首都,我们的工人阶级,有百分之二十多,占城市人口的。你北京市就占3%、4%,你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首都啊。说这一下子这是个问题。
所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还讲了一句话,就是看到游行队伍里面的工人阶级比较少。毛主席就说刘淇是北京市第二副书记,就说难道首都要搬家吗,要搬到上海去吗?所以那会就很紧张,赶快就上重工业,上首钢,搞这些东西,上面还说还是方便中央领导熟悉工业生产,因为他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干部。然后这样北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全国工业门类是130多个,北京就有120多个。这个为世界各大首都罕见。所以这一下就把北京的水资源耗的很厉害。你说像你刚才讲的你这个我们那边的万泉河。它一万个泉。北京市水是非常丰富的,以前完全就是一块湿地。我当时到内蒙古那个鄂尔古拉,就是成吉思汗他们老家的那个地方,我就看到那一大片草原和湿地,我看到时候我就觉得忽必烈那会来到北京的时候,他看到这个西海这一片,肯定就是鄂尔古拉那种感觉,因为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他是这么一块湿地。现在这湿地退的就几个水库还算是,那边还在搞开发。大马路修过去,然后我上个礼拜去看,荒郊野外空降一个巨大的shopping mall,那个完全是美国人的生活,就开着车大家跑那里去买东西,大家在那个地方都得开车。马路修的那么宽,然后那么多这些产业全往那地方去。
我看朱老师这本书我真的是很忧郁。就是这个现在是咱们朱老师也写了,咱们是靠南水北调打吊针了靠输液了,打点滴了。这两千万人口的城市啊,是中国的首都啊,就靠打吊针活着。我就说这么多。朱老师接着说。
马国川:刚才朱老师和王老师讲,我理解啊,两条,一个是上游修了太多的水库,把水拦截在外面了。第二个王老师讲的就是毛主席为了他们高兴,搞了那么多工业建设,地下水用的太多。至少是两条原因,两条很根本的就是都是人为造成的。我看朱老师的书就刚才我说的感到很沉重。其实我看王军老师的书也感到很沉重。他的《城记》包括他最近出的《拾年》,讲北京城六十年来的变迁。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美丽的在世界上都可以摆在前面的一个古老的城市,眼看到就一点点的拆没了,拆成了现在的模样。然后还有刚才王老师讲的内容特别感慨,如果我们现在还回到60多年前,我想可能在北京去转的话,可能就是王老师刚才的那个场景,当初都是水,都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就60年很短的一个时间就变成这样,我就在想不管是山河的变迁,山河破碎,还是一个城市的样子来说,变成这样一个模样他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两代人,就是我们此前,就是中华民族在这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都没有如此改变过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为什么能够把他改变成这样,而且这种改变,我觉得我个人看并不是说向一个正确的方向改变,向我们希望的美好的中国方向转变,而是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在他指导思想上很显然,他绝对不是说方向正确,出现了小的偏差,而是完全错了。他这样的问题根源是什么,这是制度的原因,还是思想的原因,还是这样一个哲学思想上有这样的错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作为记者来说我感到很感兴趣。想请王老师谈一谈。
朱幼棣:我先说。因为我想我们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这个行动的效率是非常坚决的,但是我想不是跟共产党还是跟其他党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主要是指导思想的理念的一个缺点,然后比如因为国民党他的行动能力比较差,就确定理念又做不好。但我们共产党只要一确定以后马上行动起来就是雷厉风行,我想包括对于河流、对于城市建设,对于我们建设的一些思路,理念首先是出了问题,比如说河流。那么应该说包括北京永定河,包括潮白河,包括海河,包括黄河长江,都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怎么对母亲河,如果这个关键出了问题,你一定认为母亲河是个坏河是个废河,一定要把海河根治了。这就是有问题。你怎么对待你的母亲,这个母亲可能有很多的缺点有很多的毛病,这个脾气可能比较暴躁,有一点喜怒无常。但毕竟是母亲,但母亲是不能根治的。作为一个孩子来说,那么对于母亲肯定是不能根治。我这里面写到,北京中华世纪坛的第一付浮雕,一百万年左右历史的泥河湾人民遗址就是在永定河上游,那个桑干河的边上,作为一百万年我们中国古代的文明,就是沿着河流走来的,就是河流养育了我们的文明。
应该说我们祖先是最早认识河流的规律,包括河的涨水汛期和干旱,他就居住在河的边上,包括新世纪时代和旧世纪时代,主要是沿河而居的。人类和河流始终是不离不弃的。到了这个世纪以后我们碰到了,场水灾。比如说1963年,海河流域的水灾。这个水灾可能有自然原因,也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因为那个时候修的水库比较差,都是土坝,就造死了很多人,就马上说这个是害河,那么就要根治海河从根上给你拔掉。海河是根治了。花了十几年每年都上百万人在工地上,上面修水库,中游怎么样,整整干了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把海河给根治了,根治的没有水了。然后就开始引滦济津,天津没有水了。天津是九河下游,就是首先没有水,然后就从滦河引水到天津,天津九河怎么会没有水呢,就没有水了,然后引滦基济津刚刚完,又开始引黄济津,现在又从南水北调济京。就一个工程接一个工程的干。这样干下去我看了,有个领导在里面,他从三峡调水,他说可能汉江没有水了,水不够,因为汉江上游要先往西安调水,呢北京呢?这样水不够。准备从三峡那调水。这样干下去我们还有一个休止吗?
马国川:这个是一连串的错误,看我们看宣传报上,几乎每一个都会成为领导人的政绩,根治海河成功了,是政绩,引滦济津成功了,成为一个政绩,现在南水北调又是政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朱幼棣:但这个没有认真的反思我们究竟要怎么达成要根治,海河要不要保证最低限度的生态流量。这个华北平原是不是需要白洋淀,是不是需要湖泊,这个地下水怎么办,怎么得到补充?没有一个部门从宏观方面综合考虑到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生态系统、这个水圈岩石圈大气圈的一个变化。不是说我们需要那个专家,我们国家不缺专家,需要一个大师级的人物,能够宏观的综合的确实科学的对我们的工程重大的思路思想工程和后果进行一些反思,不能够简单的有利弊,什么利大于弊。你这看不清楚,作为这个利弊对于生态是很难计算的,而且没有一个时间的距离,很难能够考虑到真正利和弊,这个不能够比较。
那就觉得这个环节很好,但是这个地方能够值多少钱,你算不出来,有些东西不好比较,不是一个层次上,所以这个我们呼唤着一些科学的觉醒,还有一个科学的真正能够有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领导。
王军:我想这个问题也是我想找答案的问题。现在这个新书的前面就是探讨一下,为什么对我们的老祖宗有这么一段时间的改变是这么的扭曲,这个刚才像朱老师说的对待母亲河是这样的一个态度觉得他有病。那么我们对待自己的文化,我就觉得我在查档案的时候看到55年对梁思成的批判,其中有一位高层领导说了一句话就是搞民族形式的卖国主义。这句话啊考考大家的智力,怎么搞民族的反而成了卖国的,我要搞西方的反映了爱国是不是?恨不得恨自己的人种不配套。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认为就是民族的就是落后的。你搞落后了,就让别人打我,那你不就是卖国吗?他们是这样一种逻辑。那么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人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那么经历了这个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日俄,就像严复写的这个《天演论》,他的书的原名是达尔文进化论与伦理学。那么赫胥黎写的,他认为那个社会不适用于这种,就说人和人之间有互敬互爱,不是那些最能杀人的人他才能够存活下去,他说个是不适用与达尔文这个东西的。那么严复是把这部分全部删掉了,就把自然界的达尔文主义全部移植到社会里面来,把别人的作品彻底阉割颠覆掉。严复还在序里面写说翻译要做到信达雅,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很不是那么回事,你可以不写那个序,把别人的东西完全搞混了,既不信也不达更不雅了,那个时候是不是把这样一种达尔文主义植入到中国人心里面,就觉得看自己老祖宗的东西什么都别扭。
马国川:就是变成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
王军:对对。就是这种丛林法则。就是那种笑贫不笑娼这个样子,现在就是登峰造极了。你说我写的《拾年》那本书,我是按照顺序把在新华社十年的文章我把他归置在一起,我写的最早的文章是拆曹雪芹故居,最晚的是拆梁思成故居。这简直是什么概念,比方你去问一个法国人,你们是不是要拆雨果的故居?那英国人是不是要拆莎士比亚的故居?我们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就是这个东西在不断的演绎,演绎到最后一种逻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规则,用了一段时间他就产生了既得利益,他永远是会拿到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说爱国,等等事情来说事。
朱幼棣:然后就说这叫做危房。
王军:对。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一种坏现象,这是我的一种理解,就是在文化上就说我这个,他好象对我们的祖先实际上还没有很好的整理,胡适先生说的这个叫做整理活物,再造文物。首先要整理活物。你的传统的文化有哪些东西,这些东西包括像治水。我看到朱老师写到都江堰,他那会在主持这个论证相关的工作。希望媒体来反映这个事情,你这个是一个大悲哀,你说在都江堰这么一个工程上来干这个事情,那真的是有系统的来否定我们的传统。而且是完全失去了一种起码的逻辑和理性,我觉得是这样,对北京城这种连续的拆除,甚至在五六十年代还做出要拆除故宫的计划。这个有系统来否定我们的过去。对我们的过去是什么缺乏一些最起码的研究,你比如说北京。我就觉得这个城市我不愿意用情感,我可以把情感全部抛掉,我就说这个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北京好多的规划这个城市要住一千万人口,那这一千万人口是怎么来的,有没有跟水的供应有关系呢,还有要搞重工业有关系,没人去想给毛主席一句话,毛主席说就是一千万人吧。
那么在档案馆里一查那些档案。我就看到有些知识分子在五七年反右之后让他写检查说他说的话。那么有一个就是对黄河有关系。我看了之后真的是可以说是哪个朝代能够做到黄河请。那时候搞三门峡,就是说他把黄河的水全部拦住了,那往下流出去都是清水。
马国川:当时我记得我看文章说。胡乔木还写了一片文章。文章里面我有讲说黄河清圣人出。就是说黄河清了以后圣人出了,这个圣人是谁,就是东方红。
王军:所以你看这个往下游流的都是清水了。上游的我们植树造林。我看这次朱老师写三峡也写到朱镕基总理很着急啊。说现在长江也跟黄河差不多,都是泥沙问题,你说上面植树造林,五十您够不够,六十年够不够,根本不够。还有说上面实行植树造林。慢慢的水土保持就是新水了,下游的这个流下去的也是清水。那是多么大的一个悲剧。 我今年国庆节的时候我去看永乐宫,那是我第二次去,我觉得在座的朋友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永乐宫。他是元代的建筑,他里面的壁画不得了。壁画是用无道子的那一派的壁画,他画那个神仙头巾的飘带飘到地下一笔画下去是三米三,中间都没有接口。就那个师傅带着他的弟子在那里画了二十多年,但是现在永乐宫就是因为三门峡给搬迁了,搬迁了之后费了很大的力气把那些壁画切割,都能看到那种痕迹,都很心痛。然后搬到那个地方去,从永和镇搬到芮城。就搬过去之后,永乐镇那地方根本就没有淹。那个三门峡就失败了,然后那个遗址还摆在那里。这个想起来这种愚蠢。
朱幼棣:《后望书》这个序言我就写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永乐宫的这个。我们电视里面经常放,因为在周总理的关怀下面,把永乐宫给搬迁了,没想想三门峡修水工程,淹了多少古城。六座古城,很多的古迹。这个房屋被拆了抢出了一件家具,现在电视上不停的播,这个永乐宫当时总理怎么关心这个,这个人员做了什么。当然这个大伙被水淹了拆除这个房子,抢出了一件家具是很难得的,也是很值得表扬的。但是这个房子怎么被拆了,应该被谁拆了,没有人考虑过。
王军:所以说我看了之后包括像朱老师写的那个新安江的那个,淹了那么多古镇,那么多老百姓,结果最后产生的效益就相当于一个小煤窑。我就觉得这个书太重要了,太重要在哪里?披露了大量的事实,大量的被一些虚假宣传所掩盖的事实,我就觉得真的是朱老师做这个工作太重要了。其实这个我们干这行的就是要把大量的事实向社会公映。你早点公映就会改变。我就看到朱老师在后期里面写的司马迁,很巧合,我在我的《拾年》那本书里面也写到司马迁。我不知道朱老师是不是赞同,我就觉得司马迁就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他为了写史记到大半个中国都实地的调查和采访,为了写孔子还跑到孔子的故里去采访。你说他那时候多惨啊,他那时候为了把史记写完,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就写司马迁,后来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司马迁他生活那个时代也是文化堕落的不得了的时代。
为什么?那个时候焚书坑儒啊,那会纸张还没有流行啊。就把那个没有多少读书人焚书坑儒了,你说司马迁他读一个《左传》,《左传》是一个简书啊,要买一栋房子呢,他把一个房子的一个简翻完才把这本书看完,所以那时候没有多少书,被焚了。所以那到汉朝你看那个时候人跟人怎么称呼,都不太会了。我就想到我小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要文明用语,请、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从那个时候开始学,我了解的汉朝那会也差不多这样,他比我们还惨在哪里?连立法都搞不清楚。后来司马迁他们又去修立法。后来他们就治这个史记,如果史记不搞出来真没有中国,就大家没有一个集体的记忆,所以我就觉得你看一个书写历史的人他能够向社会供应历史的人,他能够对这个民族这个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是这样的一个贡献。
马国川:王老师有一个发现啊。就是司马迁也是一个记者。刚刚这个话题我觉得挺沉重的,就是说回顾这一段历史,面对现实,就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不可逆转的一种灾难性的痛苦,北京城,不可能在回到原来的状态了,今天的那种山河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秀丽山川了。刚才朱老师他给出答案最后可能在思想上,希望将来出一个大师,英明领导人,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王老师也是在思想文化上找原因。我觉得除了这些之外应该还有些制度上的原因,比如说,为什么一个人一句话为了他的高兴,就可以把所有的工业集中到一个地方上来。我最近刚看了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写的一本书。罗瑞卿,当时他都是要出席常委会会议的。后来毛突然有一段不让出席了?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毛岸青的老婆绍华要下面四青工作。罗瑞卿说你别去,你要照顾毛岸青,绍华一定要去,结果这个罗瑞卿当时挡不住他了,就让他去了。毛听说之后非常不高兴,这么一来谁照顾我的儿子啊,不要参加常务会了,就一句话,就可以不参加常务会了。过了一段绍华回来了,毛又高兴了,又让他参加常务会了。这是最高层这种决策的这种随意性质,我觉得恐怕不仅仅是从思想上来找原因,还有一个制度的原因。就我前不久采访联想的柳传志,他讲的一段话非常好,他说西方的制度他运行的很好,但是还不是最好,他大概能打个七十分、八十分,打不到九十分但是也不会到六十分,中国这套制度如果一个好的决策搞好了可以打到九十分,但是一个坏的制度就可以0分甚至还是负数。这就是制度的差异性。
刚才在想朱老师和王老师讲的这样的思想的原因,包括一些专家的问题,这本书里面也讲到了地震。朱老师用四个篇幅讲地震,08年地震的时候很大的一个处境。我记得当时我看完我特别关注,我作为媒体人特别关注,但是主流的原因专家讲的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纳闷。因为我小时候学过有那么一点点,现在完全不是了。我当时就在想你要地震专家干什么,我当时也想写说批驳这个,但是呢觉得我不是专家,我说不出那些话。可是看到这本书我觉得找到了朱老师可以和这些人对话。
他揭穿了很多所谓的地震专家的谎言。我想请教朱老师说,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地震这个问题你到底怎么看?到底将来是不是可以预测的。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福祉。
朱幼棣:我想用李四光的话。他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当时刑台地震以后国务院召开一个紧急会议,就是地震能不能预报的问题,当时也有专家提出是地震不能预报,国外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大家争论面红耳赤。总理就问,他说,大家话讲完没有,讲完请李四光说说。他跟总理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而且他说不要议论纷纷,兵已渡河。他说把地球比成一米大的打球的话。那么地震发生在地壳上就是薄薄的一层纸。他说地震是在地壳的浅层发生,五公里到十公里的这样子,就是跟地球一米大球,他就是纸一样的厚度,而且地震并不是分散在地壳上面的,平均分散很多点肯定是不好预层,如果像鸡蛋一样,如同鸡蛋破了的壳,那么地震就发生在破了壳的上面,就是断裂带,那么你可以观察那些断裂带是活动那些是不活动,而且长期进行检测。那么必定能够找到预报的途径。
我觉得李四光是对的,他还讲到了四川川西的问题这个断裂带怎么形成的,要怎么密切的关注。而且我们当时出了一些政策,包括群防群治,包括专家包括大学生,用全社会的力量,来监测地震。确实这个地震有很多的很难,特别是他有两个概念,中长期的一个预测,一个是临震预报,这个临震预报是特别难的,就是半个月一个月以后发生,这个预报是比较难度,这个预报是中长期野外调查和中长期基础上搞的。可惜的很,现在我们进入了商品经济的时代,这个地震行业要跑野外,他吸引不了我们优秀的人才,也吸引不了优秀的学生,可能待遇也比较差,这个从事地震工作或者地质工作很多人都不安心,而且况且你可能这一辈子研究了这个地震也不可能发生,蹉跎岁月。一般人看来这个东西是甘于寂寞的行业,要很深入的研究地质的问题,要跑到野外,搞调查,现在地质系统大概是有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就是原来中科院的搞地质的,地矿部搞地质的。这是地震地质的研究,另一部分是原来的国家地震预报的东西,就是搞地震仪的临震记录的,地震仪可以测量哪个地方发生了几级地震,是搞监测的。从现在看搞检测的比较有钱,他可以申报国家的课题。他搞计算机搞什么网络,固定设备这样,是地震行业里面活的比较好的一部分。而且这里面可能掌握了部分话语权的部分。因为他坐在室内做的能够申报课题又能够申报国家的投入,你跑野外你到处跑也弄不了几个钱还很辛苦。
搞检测肯定是马后炮为主,因为发生地震以后才有记录。这样搞预报的搞临震预报的人才特别短缺。现在这些为推卸责任也好,干脆说国际上都没有解决我们解决不了,国际上当然是难,那日本上还有海底的那个,跟我们大陆是不一样。海底你肯定是预报不了,他这个断裂在海底,不在我们大陆上面。但我们中国的断裂带应该说几条还是应该在大陆上,比其他国家要有利的多。我想周总理也说,跟大学生说,我们这代人可能解决不了,但是我希望你们这代人能够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对行业,特别是对地震科这个志气信仰很重要,世界上没有干不成什么事。如果有这个信仰就一定能够突破,如果老是无所作为,这个世界难题就解决不了,那么就一定通过不了。因为我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成功预报的海城地震。
王军:我这个没有什么发言权。刘巍在这里,他对海城预报包括汶川地震之前的地震预报工作的状况,他是作了一个非常系统的调查。当然我是他那些报的编辑,我在看的时候也是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地震怎么预报的问题,因为有很多说法叫做地球不可侵入等等,我看了朱老师这本书有一个李四光这样一个分析,是浅层的这个地壳的活动状况,这个是有很多办法是可以检测的。那我就觉得像五李四光包括周恩来他们做这个决定他们确实是有一种历史的使命感,我就觉得对这种事情负责任的政府的官员,他有没有在这么样一种状态。我就觉得大家都是怀疑,后来这本书里面事实上他们是为开拖责任来反驳他们,我就觉得看这些的时候真的是让人感受非常的动怒。
马国川:我理解刚才朱老师还有王老师讲的这些问题其实涉及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科学态度,科学态度其实以前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认为人定胜天,人可以改变一切,包括改变山川面貌,更不要说改变一个小小的北京城了。现在我觉得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也打着科学的名义,但是实际上是利益的在背后驱动,部门的利益,个人利益,包括说什么这个不可预测,那个不能做,或者说这个可以拆那个不能拆,实际上背后并不是什么所谓的科学预测,但是一些人以专家的身份,以科学的名义在那里做,背后是利益驱动,是不是这个问题?
朱幼棣:关键是不是敢于担当、面对的问题,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或者地质学家,地震学家敢不敢担当,敢不敢面对,这个李四光有一句话比较好,就是云南地震他没有预报出来,就是李四光国务院开会的时候说最近发生在云南一次地震,地震以前是有先兆的,可是我们没有预报出来,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要将功补过,把地震搞好,他说自己是有罪的人,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有这分担当,人民也会理解也会原谅的。现在马上来了一个就是怕自己承担责任,就开始躲了,就不能预报。这是地震前一点先兆也没有,就是有先兆,四十分钟以前就发生了一次地震了,也不行。有先兆不行,没有先兆不行,总而言之先把他说不能预报。然后就无所作为了。我总觉得作为一个科学家也好,作为一个行政部门领导人也好。要有一份担当。李四光说的非常好,如果地震永远都不能预报的话就成立这个部门没有必要了,我们这个工作就没有意义了,那么你不需要成立这个部门了。
那么我想有人成功的先例,只要努力工作还是可以预报的。为什么这次把意大利的学家判了刑。我觉得判的非常好,因为以前发生了很多的小的地震,结果跟地质学家商量,问大家近期有没有大地震,最后商议后说没有。你为什么知道没有,没有也是预报,你预报了没有,其实死了人了,死了一千多人,那对工作不信任。那么这就出了问题,虽然国际上很生气,联名说地震学家是判刑是不对的,但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你要不预报不出来,还搞不清楚。
王军:他特别有意思,之前就是说没有预报,然后一下子有了,这个是不可预报的。不知道是什么逻辑在他们心里发生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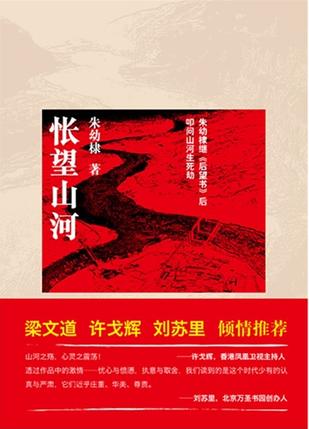
11月25日下午14点,由《财经》主笔马国川主持,以”河山不能承受之重“为主题的对谈,在字里行间书店(德胜门店)举行。著名学者、作家朱幼棣携新书《怅望江河》与新华社高级记者王军,就六十多年来山河变化,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的原因,展开讨论。因放不下对社会的责任,朱幼棣多年来锲而不舍对这些问题展开追问,回望历史,剖析当下,在对谈间,他还提到了许多被隐瞒、被忽略的重要真实事件。以下为当天对谈的现场速记,未经讲者审核,如有疏漏,敬请谅解!
对谈中精彩摘要:
需反思警惕周围的话语,例如,"抗旱防汛"的提法就有问题,什么是"汛"?汛是江河在一定的季节涨落,汛期并不是水灾。再如,二氧化碳只占大气的万分之三,人类能影响的不过万分之一,然而目前人类社会已被碳所绑架,动不动就低碳社会,甚至要收碳税。----朱幼棣
如果《史记》写不出来,真没有中国,大家就没有一个集体记忆。所以我觉得,看一个书写历史的人,能够向社会供应历史的人,就看他是否能够对这个民族、这个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是这样的。---王军
当日现场记录:
马国川:谢谢各位朋友,今天天气不太好,而且因为今天搞马拉松,很多地方交通管制。大家到这里来肯定不太容易,我有一个朋友是中经报记者。曾经做调查,北京一年的交通管制七千次,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二十次。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个当过委员长的,在全国常委会里面。有一次他就说,你们老是说北京堵车,我觉得不堵啊,我每次到走长安街都很舒畅啊。你们以后应该实地调查,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我们来开始比较沉重的话题。《怅望山河》这本书我是周三上午拿到的,到晚上就读完了。读完了之后,非常感慨,文笔非常好,但有一个缺点,看了之后心情特别沉重。真的是特别沉重,就没想到,今天的中国,我们在北京,有时候我做记者可能走的地方多一点,周围朋友可能也走了很多地方,我们走很多地方没有这么深入的去探讨这个国家这么多年来山河如此巨大的一种变迁,而这种变迁,不是按照我们所想象的,向一个更美好的方向发展,而是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发展。大江大河断流,山川断裂等等,这一切问题这本书里面都有反映。
我想是不是首先先请朱老师先谈一谈他到底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是怎么写这本书的?
朱幼棣:因为我写这本书,前后时间经历了五年之久。五年以前,当时出了一个《后望书》,讲到城市的文化遗产、城市风格和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讲到了一些江河水利的问题,是和江河以及跟工程建设有关的。但是当时写的比较匆忙,有一些话还没有说完,一些重要的工程重要的关键字也没有说完。我记得当时跟王军在书店做节目,就有人提出来,说我怎么对长江三峡这么重大的问题都没说。我说我当时已经开始接触了那部分,那时候还没有进入后三峡时期,而且后三峡时期还没有到。很多这东西看的不是很清楚。但《后望书》的最后一节已经讲到了长江三峡问题,我就开始准备写这本书。这本书准备过程正好碰到了汶川地震,汶川地震应该说是一场我们的重大灾难。汶川地震以前,我正好考察和调查世界文化遗址,也到过都江堰的一些地方。那个时候工程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地步。当时提到了岷江水电,岷江河流都完全干涸了,那时我就想,是不是跟地震有关,当然是可能是一个大体构造的变化。就开始研究地震问题,地震虽然有多种原因造成,但是人为的工程因素也不能够完全排除。
当时我就写了一个关于汶川地震的地质方面的思考,到底我们的地震,也是一个山脊平衡被打破了。这个突发地震有多种原因,有自然的因素,有月亮的因素,还有可能有工程的因素,都不能够排除。我有一个特殊情况,年轻的时候搞过地质。二十几岁的时候在矿山做技术员,看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地质的书。后来我到新华社做记者,跟王军同事,我也是是国家荣誉地质队员,这方面也低调。然后就开始深入就讲、写地震的,比如地震我们应该注意什么,特别是工程建设重大工程建设怎么能够保护我们山区的平衡,使我们江河和山体不受破坏。这就写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写了《大国医改》,把中间断了有一年多时间。既然讲江河问题,那主要的江河应该有。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究竟是水灾,还是洪灾还是旱灾?我们江河面临着什么?应该说,北方的江河面临的主要的问题是断流和枯竭;中部地区和南方河流主要是污染,而且地下水不能饮用。这样我们就从一个宏观层面,考虑到研究我们主要江河这个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一些变化,这跟我们工程建设,我们治理的指导思想有关。为什么现在海河完全断流?天津原来是一个河口、港口城市,现在天津没有港,海河不能通航,都是近五十年来发生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因为五十年就是两倍人的时间,我们现在刚生下来就认为城市就是高楼大厦,城市就是现在我们的就这个情况,现在孩子觉得河流本来就没有水。这个北京的永定河就是没有水,北京就没有河流。但实际上,历史不是这样的,是我们半个世纪以来,一步一步造成的一个江河、这个山川面貌的一种变化,我想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