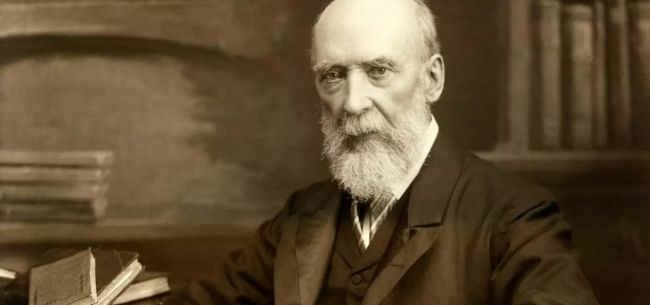
(赫德 图片源于网络)
史稷/文
文化身份与职业选择
西方人在中国的跨文化经验和文化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职业选择。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的西方人大致可分为三类。
首先是西方外交官或那些在政治上依赖西方政府的人,如各国记者。
西方外交官受雇于其政府,必须代表本国政府的利益,维护本国政府的政治立场。只要他还在外交部门工作,就不能在其政府和中国之间的任何关系上观点暧昧。他的政治认同避免或者掩盖了文化身份的模糊性,他不需要担心自己会被本土社会排斥,也不需要担心自己无法进入中国官场。他可以赢得并被视为中国的朋友,以自己的魅力为文化之间的理解做出杰出的贡献,如浦安臣 (Anson Burlingame,1820-1870)——恭亲王称赞他是一个“有荣誉感而平和的人”,但他仍然是他本国——美国的代表;他可能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成为像威妥玛爵士那样的杰出的汉学家,但他必须注意不能把对中国文化的迷恋与政治混为一谈。正如威妥玛的传记作者詹姆斯·库利所说,威妥玛对发展双重文化外交的支持,使他特别容易受到过于亲华的指控,“他的政策立场受到怀疑,就像一百年后,许多美国在华专家的忠诚度在麦卡锡主义影响下变得可疑一样。”库利补充说:“威妥玛的批评者将他描述为中国排外人士的帮凶,他对中国文化的学术兴趣使他几乎成为英国利益的叛徒。”总之,外交官即使成为中国通,也必须小心翼翼,不要让人觉得他的忠诚趋于分裂。
不难想象,那个时期在中国的大多数西方记者,大都只在条约港口的欧洲人圈子里活动,他们无法深入中国内地,与中国人的接触很少,难以深入中国社会。他们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消息主要来源于领馆、买办和翻译:“在上海酒吧喝酒或在赛马场闲聊时,他们把错误的信息和推测混在一起,通过信件、日记回忆录、游记、外交报告和新闻报道传到地球各个角落,在那里被接受为事实。”美国历史学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他关于慈禧太后的《龙女》一书中写道。最典型的是苏格兰裔澳大利亚政治家和记者莫理循(GeorgeErnestMorrison,1862-1920),作为《泰晤士报》驻上海的通讯员,他声称自己不用学中文就能了解中国事务,《北平隐士》的作者休·特雷弗·罗珀称,因为“莫理循对于《泰晤士报》的巨大价值并不取决于他对中国的了解,而是取决于他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之目的的了解。在英国,中国并不是新闻,外国势力对中国的渗透才是新闻。”
其次,晚清时期有一些独立于西方和中国政府的探险家和专业人士。他们没有义务为其政府的政策和行动辩护,也不对清廷负责。如传教士、记者、商人、学者、医生、工程师等。
一般来说,传教士通过建医院、办学或办报等方式与中国社会保持密切联系,希望通过迂回的方式掌握中国人的心理,让他们接受基督教。他们中许多人最后把中国视为第二故乡,靠着不可动摇的基督教信念在两种文化之间保持平衡。这样的传教士不胜枚举,留下许多佳话。
商人可以通过了解客户的喜好来提高销售量,但多数在华西方商人当中并不努力了解中国习俗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当中国买办进入中西交融的文化层面时,西方商人仍然处于相当单一的文化环境中,也不会为他们的文化身份而困扰。
还有些在华西方文化人不需要对任何政府承担责任,也没有终极目的,脱离了原生社会,而又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员,就可能失去文化认同,成为两种社会和文化的弃儿。最典型的莫过于“北平隐士”埃德蒙·巴克豪斯(SirEdmundTrelawnyBackhouse,1873-1944),他被同代人认为是一位对满清宫廷了如指掌的杰出的爱尔兰东方学者,但实际上是一个变态的骗子。巴克豪斯在北京生活了45年,通过幻想他与慈禧太后的性关系来吸引西方公众的注意力,声称他得到了慈禧的宝贵的珍珠项链,成为丑闻人物。他在北京时远离西方人,碰到西方人就用手帕遮住脸,拒绝所有社交。他穿着“长长的白色丝绸中国袍子,胡子留得又长又密,最后也变成了白色,直到他看上去像一个可敬的圣人。”回国后,他与姐妹家人在家乡班夫郡和爱丁堡居住期间,“穿着中国式的袍子行走,令班夫郡当地人和爱丁堡循规蹈矩的公民惊讶不已。”休·特雷弗·罗珀说他“前半段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如何伪造满清宫廷种种细节,后半段大部分时间用于鼓励其他人如法炮制。”最终他与中西两个世界都格格不入,成为一个古怪的边缘人。
第三类就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为中国机构服务,成为朝廷顾问的西方人。他们在中国官员的著作中,在中国近代改革进程中留下了很多印证。西方人受雇于中国政府,其作用是帮助中国在外交关系和贸易中与西方人打交道,同时不损害西方政府的利益。他的职业、地位既不允许他作为典型的欧洲人行事,也不允许他彻底转变为中国人。为保证成为对中国和欧洲列强都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别无选择,必须成为一个调解人,因此不得不持有双重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与双重角色
1863年至1906年担任中国海关总署署长的赫德就是这样一个典范。作为领导一个多国人员机构近半个世纪的人,赫德是研究19世纪下半叶在华西方顾问绕不过去的人。他也是近代中西交流史上各种复杂关系的枢纽。赫德日记的编纂者这样精辟地概括他的地位:“作为一个多国语言机构的负责人,他是一个多种意义上的文化中介——生为英国人,选择成为中国人。在这个位置上,赫德参与各种谈判:在机构中的中国和西方雇员之间;在西方商人和中国官员之间;在中国和西方官员之间,以及在西方官员之间。”19世纪60年代以来,清朝与西方大国之间签署的几乎所有条约上都留下他的痕迹。清廷经常听取他关于现代化步骤的建议,第一批中国驻外使馆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赫德。他得到了作为一个出身贫寒的爱尔兰男孩在自己的祖国无法获得的一切:他被13个国家授予24次勋章,达到了作为文化中间人职业生涯的顶峰。
马戛尔尼爵士是另一位获得清政府信任的爱尔兰人。他曾对戈登将军说,他的野心是“在中国,并最终在北京具有南怀仁、汤若望和其他天主教传教士在康熙和乾隆统治时期拥有的地位和影响力。”虽然说他在权力和荣誉上比不上赫德,他还是部分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他被李鸿章任命在松江建立兵工厂,后来又被任命管理南京兵工厂。1876年至1905年期间,他作为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英文秘书帮助第一批中国外交官熟悉外交惯例和欧洲习俗。
法国人日意格曾在给拿破仑第三的信中表示,他正努力扮演为中法工作的双重角色。当李鸿章在技术上依靠马戛尔尼,在外交方面依靠德璀琳时,他在南方的同僚和对手左宗棠,则倚重两个法国顾问德日碑和日意格来建造福州船坞,这是他的“自强”项目之一。在日意格的指导下,船坞共生产了15艘蒸汽船。此外,在总督沈葆桢的支持下,他创办了船坞学校并组织赴欧教育代表团。朝廷当然也没忘了为日意格受勋。
获得清朝政府认可的西方人都有一些相似的性情和跨文化的经历。
一位与赫德和马戛尔尼熟识的女士注意到,他们处事冷静而韬晦,“不为急躁的愤怒和不耐烦的言语所动”。他们知道如何避免令中国官员恼火的西方人强加于人的方式,尽管原则上他们是有道理的。他们时刻注意那些思想开放的官员何时易受中国社会保守势力的诋毁,也深知中国哪些法律和社会行为是西方人不能容忍的。
很多在华西方人的种族优越感,使得他们很难接受在一个中国人的领导下工作。赫德的前任李泰国(HoratioNelsonLay,1832-1898)的声明最为典型,充满歧视:“我的身份是中国政府聘用的外国人,为他们完成某些工作,而不是在他们手下。我无需指出,一个绅士在一个亚洲野蛮人手下干活是荒谬的。”法国人德日碑也不愿接受以下属的身份在中国人手下工作。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William M Lang,1843-1906)辞职的原因之一,是他不能作为任何中国官员的下属为李鸿章服务。但即使大清帝国已经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也不能容忍西方雇员如此傲慢。赢得朝廷信任的西方顾问则表现出对中国的责任感,忠诚于朝廷。日意格“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雇员,仅此而已。他认为自己在船坞的作用是有限的,并始终认为自己要对沈葆桢负责。”赫德对其下属反复强调:“海关是中国的机构,而不是外国的。因此,每个成员都应对中国人——包括人民和官员——负责,避免行事有所冒犯和令人不快。每个人首先要切记的是,他是中国政府的有偿代理人,负责执行特定的工作,他最该关心的是做好这项工作。”这或许就是上海话“拎得清”的意思。
作为欧洲的世界主义者意味着在西方列强的冲突中保持中立,更容易被中国当局接受,不仅可以丰富自己的社会生活,而且可以拓展自己的职业前景。欧洲顾问在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采取了多元文化的姿态。世界主义是海关总署的招聘原则之一。在赫德的势力范围内,有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美国人、俄罗斯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日意格很受赫德赏识,因为他“有进取心,勤奋,聪明,能干”,尤其是懂得“在这些地区谈论世界主义的价值。”至于德璀琳,他是“完全站在中国一边的德国人,既不激烈地支持德国,也不明显地反对英国......”戈登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宣称,如果中俄之间爆发战争,他将放弃英国公民身份,以便在不妨碍英国政府的情况下为中国作战。
然而,他们的忠诚有时不可避免是双重的,甚至分裂的:试图忠于清政府,又忍不住表现出爱国主义。当赫德被要求解释他在中英之间的立场时,他回答说:“我处于骑墙状态。我不允许自己倾向于任何一方……但毕竟我是英国人。”也就是说在中英冲突中他将站在英国一边。马戛尔尼被称为“内心深处的中国人”,但他坚持认为,第一位中国驻欧洲公使应乘英国国旗下的英国轮船进入英国,而不是按照原来的安排乘坐法国轮船,尽管乘坐英国轮船行程会更长。这个建议被当时的英国公使威妥玛称为“灵活地把爱国主义理想引入一个普通的方案。”威妥玛因此断言:“马戛尔尼博士还是个英国人。”
在华成家立业,还是只为了职业生涯在华居住,这个问题影响了西方顾问的婚姻和后半生。虽然赫德之所以功成名就,是因为他长期在中国工作,但实际上他并未做好在中国度过一生的思想准备。孤独和思乡之情贯穿他的一生,他一直没有放弃离开中国的想法。他在给伦敦办事处的代理人坎贝尔的信中写道:“我想离开中国,我真的很累:我不能永远坚持下去。我很孤独,因为太忙而无法真正或有意识地感受到。但是,孤独是我存在的底色。”他一直深深地怀念他在北爱尔兰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氛围。这可能是他最终与家乡的爱尔兰女人结婚的原因之一,尽管他与一个中国女人阿瑶有十多年的交往,阿瑶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他对阿瑶也一直怀着温柔的回忆;尽管为邻居的中国女孩所吸引;尽管他的中国同事总在建议他娶一个中国女人为妻。除了与家人一起在中国的短暂的快乐时光,赫德一生伴随着孤独感。
而马戛尔尼则很快决心在中国定居。当他确信只有在中国才能实现他的抱负时,他就为自己在中国生活制定了一个完整的规划。他的传记作者说:“他认为,如果采取通常的做法与自己种族和宗教的女士结婚,就会在自己的道路上设置障碍,而且他很可能会因自己的行为而破坏他事业成功的机会,这一事业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是艰难而危险的。”因此,他按照中国的礼仪娶了中国妻子。这样,马戛尔尼“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中国人中间安放了他的家和他的野心。”对赫德来说,情感、婚姻和事业是分开的,而马戛尔尼则把婚姻和事业联系在一起。马戛尔尼未像赫德那样爬上权力的顶峰,但他也没有像赫德那样一生被深入骨髓的孤寂困扰。
基督教信仰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追求个人利益的信念并行不悖,是19世纪西方社会道德的粘合剂,尤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体系的支柱,一个维多利亚人必须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中许多人即使不是传教士,也具有传教士精神,传播基督教是他们的共同理念。李提摩太虽然受雇于中国政府,但他本人从未脱离过教会。戈登是一位“军事传教士”,相信“通过引进西方的进步,可以将基督教的影响带到中国。”赫德从未脱离传教士的环境,经常提醒自己基督徒的价值和使命,他的日记中充斥着信仰上帝的表达、对牧师祷告的评论或对照《圣经》的自我审视。
综上所述,晚清在华西方人文化认同的蜕变,与条约港口的文化环境、欧洲本土社会的价值观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分不开。如果说晚清在华西方人大都停留在中国社会的边缘,那么清政府的西方雇员则处于中国社会的中心。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外国人中的大多数,并不需要质疑自己的责任与忠诚。而为帝国朝廷效力的西方人,每时每刻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要扪心自问:面对中国和他们的祖国,他的决定是否正确。他们不得不在西方和中国的价值观和制度之间寻求妥协。在两个国家和两种文化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的唯一方式,就是持有双重文化认同。然而,这种双重身份并不意味着两种价值体系的综合,而意味着受到两种并不总能和谐相处的文化的强烈吸引,不免伴随着撕裂感。因此,保持双重身份不仅需要对两种文化和社会框架的深入了解,还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和精神支柱。就此而言,为晚清政府效力的欧洲顾问,是在华西方人中极少数成功地操纵双重文化认同的双栖人。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